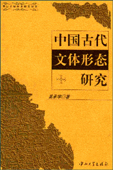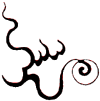|
傅璇琮
關于今年四月間,吳承學先生來信,約我為其新著《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寫一篇序。剛看到信中所提的書名,馬上就想到明代兩部文體學的著作,即吳訥的《文章辨體》和徐師曾的《文體明辨》。《文章辨體》詳列歌謠、賦、樂府、詩及各種駢散文體五十九類,《文體明辨》更細分為一百二十七類。當時我很擔心吳承學先生如何把中國古代如此繁復、瑣細的文體作統括全局的概述和分類辨析的細研呢?后來接到來稿,先翻目錄,不禁眼光一亮,原來全書十七章,第一章至十二章分別選擇了先秦盟誓、謠讖與詩讖、策問與對策、詩題與詩序、題壁詩、留別與贈別(詩)、唐代判文、集句、宋代隱括詞、明代八股文、晚明小品、晚明清言等文體進行個案式的清理與研討,第十三至十六章則對文體學理論作歷史性和邏輯性的梳理,最后一章則以獨特的視角對中國古代以評點形式所顯示的文化傳播與文化普及行為作出頗有當代意識的評議。以上章節,大部分在前些年曾以論文形式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過,當時我也讀過幾篇,這次為了遵囑寫序,就集中把全稿細讀一遍。每讀一章,說實在話,真有一種藝術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論議深沉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悅。
我想,書序這一文體不是書評,不必對書作全面的介紹和評論,--此書書前的"緒論"也已對本書的宗旨作明晰的闡釋。書的序言應當是一種較為自由的文體,大致是撰寫者的一篇讀后感,可以對書作感想式的評論,也可與著者作學術上或友情上的交流,也還可抒發撰序者本人的某些感慨。就我個人來說,吳承學先生比我年輕約20余歲,按照友人蔣寅先生《四代人的學術境遇》所述,在20世紀古典文學研究行列中,我算是第二代,承學先生算是第三代,但我總有一種與吳、蔣都是同一代的感覺,因此每一次在學術會議上,彼此都能促膝而談,也無"忘年"之感。這樣,我這篇序也就隨意而談,無一定之體。
關于我讀這本書,以及讀《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晚明小品研究》,曾于燈下默想,承學先生治學有怎樣一種路數?于是得出八個字,這就是:學、識貫通,才、情融合。再演繹為四句話:學重博實,識求精通,才具氣度,情含雅致。我認為,博實、精通、氣度、雅致,確是這些年來吳承學先生給學術同行的一個總印象,也是承學先生一輩中的前列者這些年來在其著作成果中所顯示出來的藝術才能和精神素質。
關于將以上的八個字、四句話,具體落實到這本書,首先我覺得承學先生有一種堅實而敏感的學科建設意識,而學科建設也確是當前古典文學研究界面向新世紀所必須正視和承擔的理論課題和實踐項目。十多年前承學先生在復旦攻讀博士學位時,就提出"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并寫有專著,經過近幾年的潛心研究,又提出中國古代文學文體學。我認為,這不只是針對目前學術界對文體形態研究的薄弱情況,更重要的是有鑒于文體學研究對于整個古代文學研究有不可忽視的完整學術結構的意義。正如作者在書中不止一次的說到:"我的研究目的是回歸到文學自身,從文體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往往把文體單純看作一種形式技巧,不予重視,這是出于一種偏重所謂政治因素的誤解,從而限制研究的視野。如果按"緒論"中所說,我們在建立文體學的過程中,全面研究古代文體的內部結構、文體的審美特征,以及文體之間的互相影響、互相融合、文體發展的規律等等,并在此基礎上,研究文體所反映出來的人類感受方式和審美心理及文化心態,這就能促使我們古典文學研究的整體推進。
關于當然,作為學科建設,一方面要有科學規范,另一方面更要有重點突破的創新意識。以古代文體學而論,面對從先秦至近代三四千年間幾十種、上百種的文體,要一個個排著隊來評述,談何容易,這也是古代文體學面臨的一個客觀難題。但我們可以作主觀突破,這就是本書的一種創新精神,即先不作系統的概論,而是對過去長時期不受重視而實有文化涵義的包括文學文體和實用性文體,從文體體制、淵源、流變及各種文體之間相互影響等等,"作歷史的描述和思考"。我覺得這樣作,對當前學科建設來說,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我們不要先作大而全的概述性工作,這樣難免重復、淺層,先選擇有一定代表性的幾個點,作精細而又有高度概括的探討,這就能使這一學科成為富有現代意義的、具有眾多堅實實驗室的科學園區。
關于這里提到實驗室,我以為人文科學也應該有自己特色的文獻材料庫,而本書在這方面也頗有建設性的創新點。我在上面曾講到學重博實,而就現代來說,博實必須注意利用新的科技成果。在第一章《先秦的盟誓》中,作者表示,他通過現代先進的電子檢索系統,得知"盟"字在《左傳》中出現640次,在《公羊傳》中出現162次,在《谷梁傳》中出現172次;"誓"字在《左傳》中出現22次,在《谷梁傳》中出現1次,在《公羊傳》中沒有出現。又,在《漢字游戲與漢字詩學》一章,作者從《詩牌譜》中摘下開頭三十個字,根據北京大學網站《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得出它們在《全唐詩》中出現的次數,分別是:天17614,云19029,煙6176,霞2008,霜3813,等等。這樣的"總賬"式數字統計,并不純粹是技術性的,它往往會帶給人們一種文化探索的興味。我在一次會議上也曾聽《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制作者說過一段話,他說他輸出"夕陽"一詞,來檢索《全唐詩》出現次數,結果是初唐時期最少,晚唐時期最多,說得與會者發出會心的微笑。
關于當然,對我們搞文學研究的人來說,掌握文獻材料,不能全靠電子檢索,還得靠頭腦積累,頭腦中的眾多積累和有效利用,有時是電子檢索所不能代替的,它的表現特點是"活"。譬如本書中講到判文對敘事文學文體(戲曲、小說)的影響,就舉出宋《醉翁談錄》所引用的公案小說,元代的《陳州糶米》、《朱砂擔》、《蝴蝶夢》、《灰闌記》、《竇娥冤》等十余個雜劇,明代的《包公案》、《龍圖公案》等白話判案小說。又如《晚明小品》一章述及古人以本草、藥方形式寫出富有情趣之文,所舉之例,有唐張說《錢本草》,賈言忠《監察本草》,侯味虛《百官本草》,宋釋慧日《禪門本草》,明袁中道《禪門本草補》,清張潮《書本草》(按藥方所舉例,省)。這是現在電子檢索還做不到的,需要我們當代學人,排除外界的諸種干擾,安心讀書做學問,才能有所獲得。
關于承學先生的可貴之處,還在于博通中外古今,書中好幾處引及現代外國的哲學、文學理論著作,如論集句時,引述俄國美學家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美學原理;論《詩牌譜》,就隨手聯系西方文論中的意象研究,據美國學者華茲生對《唐詩三百首》所作統計為例。更讓人感興趣的是,《晚明小品》一章中論及作者自己立名的"意象式小品",也即一連串的意象聯綴而成的小品,這些意象有時看來只是雜纂而成,而實際上則有內在的聯系,構成一種獨特的藝術意境。作者寫到此,特地舉了現代作家汪曾棋的小說《釣人的孩子》一段描寫。為提供我們搞古代的人欣賞,我這里把這段美文移錄于此:
關于抗日戰爭時期,昆明小西門外。米市、萊市、肉市。柴馱子、炭馱子。馬糞。粗細瓷碗,砂鍋鐵錨。炯雞米線,燒餌塊。金錢片腿,牛干巴。炒萊的油煙,炸辣子的嗆人的氣味。紅黃藍白黑,甜酸苦辣咸。
這樣的意象式字句,更能使人體味抗戰時期昆明郊區一個普通小鎮的獨特景致。講古代文體,引用現代文學創作,這不但是增加書中的文采,更使人得到溝通古今的啟發。我過去在論述朱東潤先生史傳作品時,曾提到"朱先生的傳記作品還有一種神來之筆,那就是在講述歷史時,忽然會把過去的生活拉到現代來,增進入們的時代意識與生活情趣",并舉《杜甫傳論》中論及杜詩《嚴氏溪放歌行》,引及近代樂曲《二泉映月》,論及杜甫在江陵的遭際,聯系法國雨果的小說《笑面人》(見《文學遺產》1997年第5期所刊拙文《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傾注》)。溝通古代文學與現代創作的內在聯系,挖掘我們華夏民族的潛在文化意蘊,這應當也是我們古代文學學科建設的一個命題。
關于我恐怕不能講得太多,影響讀者對這部佳作的研讀和欣賞。我想再補充談兩點。一是作者注意過去不大受人重視的一些文體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強調"文體其實是人類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歷史的產物,積淀著深厚的文化意蘊"。如論文字僻澀的先秦盟誓,指出"盟誓是中國古代歷史最為悠久、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文體之一";講到具有神秘意味的謠讖和詩讖,說"它們具有某些其他類型詩歌所沒有的文化內涵";說古人的題壁、題樹等題詩,"實際上已經成為古代的一種特有的文化氛圍,一種富有藝術色彩的人文景觀";講到一向被視為政治文體的判文,說"判辭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與文學意義",對一向被視為臭文的八股文,說它是"對于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生存狀態影響最大的文體之一"。這樣從文化視角來探討文體的產生、演變及社會意義,確能使人擴展視野,加深思索。另一點是書中對某些流行看法和傳統觀點,能獨出新見。如論八股文,說八股文確影響明代文人和文學的創新精神,但又指出其理論卻比較復雜,對于古代文章學、技法理論產生的影響難以斷然否定,并說作為科舉的一種文體,八股文"確綜合和融化了古代許多文體的特點";又如這些年來備受人贊賞的晚明小品,作者在作了肯定論述外,提出其一個特點是"雖小亦好,雖好亦小";對晚明清言,指出其思想內容的兩重性,即"清言所標榜的是清曠,而最終卻容易使人走向平庸、世故和滑頭"。這些都是使人愜意的中肯之論。
關于承學先生于四月中旬寄來此書書稿時,并附一信,信中有幾句話,頗值得深思:"這里遠離學術中心,在許多外地學者看來,此間不是做學問之處;而在此間人看來,在此做學問乃是不合時宜之事。這兩種看法都近于事實。既難以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也難以得到社會的承認,所以學者在這里想真正做點學問實在具雙重的困難和壓力。也許正是這樣,我的論文總是帶有某種'邊緣'色彩和寂寞之音,格格不入時流。"這幾句話我是完全能理解的。我覺得,像我們這樣做古代學問之人,是不能與股票"聯網",與"票房"比值的。我們要有一種高層文化導向的自期,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說承學先生那樣的才具氣派與情含雅致。人生總是有壓力的,就我個人來說,20幾歲時就承受過難以想象的政治重壓,現在也還不時有一些莫明其妙或所謂世態炎涼之壓,根據我早年的經驗,這就需要有一種"傲世"的氣骨。我總是以為,一個學者的生活意義,就在于他在學術行列中為時間所認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時的社會名聲或過眼煙云的房產金錢。
關于關于廣州的文化環境,最近我從上海古籍出版社送我的一本書得到新的啟示。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今年年初出版一本大十六開本的圖集:《十九世紀中國市井風情--三百六十行》。書中影印了19世紀初期廣州畫鋪中的畫師繪制的所謂外銷畫,畫師當時從營利出發,將各種題材的水彩水粉外銷畫繪制出來,銷售并流布到歐美各地。這些外銷畫所表現的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片斷題材,而畫法卻摹仿西方,現在看來十分別致,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具體情景。這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可見在鴉片戰爭這個被作為中國近代史起點之前,廣州的社會與文化風氣已有一種相當西化的傾向。社會的發展與文化的走向是一個整體且相對獨立的行動,并不完全受政治的制約和影響。陳寅恪先生早年所作的宗教史名篇論文《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就提出過一個論點,說兩種不同民族的接觸,"其關于文化方面者,則多在交通便利之點,即海濱港灣之地"、"海濱為不同文化接觸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頗多"。對讀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這本表現廣州19世紀初期三百六十行市井風情圖集,更顯得陳寅恪先生論點預測性和推導性之可貴。近20年來廣州的開放成績顯著,文化的活躍也有其他地區所不及之處,吳承學先生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他以寂寞之心鉆研其所稱之"邊緣",必將是一片為人注目的學術"新境"。--這,也是拙序的殷切期望之情。
2000年6月中旬,北京六里橋寓舍,時當數十年來未有之高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