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東 |
|||
|
【明】
陳繼儒 編集
李安綱 趙曉鵬 述論 目 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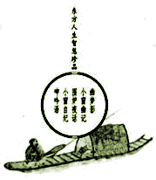 |
|||
|
|
||||
|
|
||||
| 148 談空與耽靜 談空反被空迷,耽靜多為靜縛。 「述論」 佛教存在的依據便是人們的痛苦。痛苦的根源在于執著,解脫痛苦的方法就是 破除執著。人們執著的原因,是因為外在有一個有的存在。佛祖通過自己的思索和 修煉,發現這個外在的有并不是一個永恒的存在,對它的追求也不是真實的人生意 義,所以提出了構成那個有的四大因素全是空而不實的。既然四大皆空,那么就沒 有必要再去追求和執著了。心中不再執著了,自然也就不再感覺到痛苦了。 佛教又稱空門,就是因為它講萬物皆空,萬法皆空。要使我們了解世間一切都 沒有自己永恒的體性,什么都要壞散;教我們不要對外境生起執著的心情,而使身 心不得自在。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過分地不要執著外有,其實反而執著 了空。 有些人談空卻又戀空,時刻忘不了空,這與留戀世事并沒有什么分別,同樣是 一種執著。執著了這一個空的概念,心靈上仍然不能得到真空和安靜。《摩訶般若 波羅密多心經》上說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說的就是 色和空并不是絕對對立而不可同時存在的,說到了空的本身,就意味著還有一個有 字存在著。色和空只是一種相對的狀態而已,執著于色的人不明白“色即是空”,執 著于空的人也不明白“空即是色”。 一切能夠見、聽、嗅、嘗、觸、想到的事物都是色,誰也不能說它們確實沒有 或者不存在。只是要我們心里清楚,不要執著它們就是。因為執著了有或者空,只 能帶來更大的痛苦,所以那些談空的人反而是被空給迷住了。 “耽靜”,就是沉溺在靜的境界里,結果也是被靜這個概念給拴縛住了,也是 同樣的道理。為什么要靜呢?靜與動本來就是世界物質運行的兩種狀態。只有在靜 的時候,人們往往才能更好地觀察到事物的本來面目。比如說只有那水波平靜下來 了,我們才能從中照見自己的面容;水要是在動態中,誰也看不清自己的臉。 所以,從認識自己的角度來說,讓心靈寧靜下來的確是有好處的。但卻并不是 教人整天躲到那安靜的地方,不聽也不想,不動也不吃。那樣以來,卻等于在用一 個靜字將自己的身心給束縛住了,動彈不得,又有什么好呢?真正的靜是心理上的 寧靜和安詳,而不見得非要形靜不可。只要是能在最忙碌的時候,卻仍然保持一種 安靜的心境,不被那外在的事物所牽動,就是真靜。 真正的靜是在同動的比較中產生的,沒有動就不可能達到靜,動極生靜。王建 在他的詩中說:“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維的詩中也說:“月出驚山鳥, 時鳴春澗中。”講的就是越是在動態中越能顯示出那種清靜來,這也可以說是禪宗 所追求的那種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如果我們都能夠在那紛紛塵囂之中保持著自己 心靈的寧靜境界,隨他外境千變萬幻,我自心無掛礙,才不至于耽靜而被靜縛的。 |
||||
|
中國社會出版社
|
||||
|
||||
版權所有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聯合主辦
Copyright© 2000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mailto:web@guoxue.com
mailto:web@guoxue.com
![]() mailto:yyyinxl@sohu.com
mailto:yyyinx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