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東 |
|||
|
【明】
陳繼儒 編集
李安綱 趙曉鵬 述論 目 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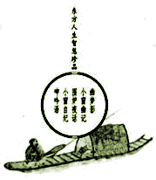 |
|||
|
|
||||
|
|
||||
|
145 會(huì)心與無稽 會(huì)心之語,當(dāng)以不解解之;無稽之言,是在不聽聽耳。 「述論」 人類與動(dòng)物的一個(gè)根本的區(qū)別,就是人類發(fā)展出了一種非常復(fù)雜而又完善的語 言表意系統(tǒng)。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概念是語言的細(xì)胞,隨著語言的發(fā)展,人類在超 越完善著自己的思維系統(tǒng)。但是,無論是怎樣地完善我們的語言和思維系統(tǒng),我們 都不能說我們?nèi)祟惖恼Z言是最完美的一種傳達(dá)方式。 因?yàn)槿祟惓耸且环N會(huì)思維和使用語言以及工具的動(dòng)物外,更還是一種充滿了 感情的動(dòng)物。在感情問題上,由于它的多變、跳躍、深淺、隱伏、轉(zhuǎn)移、即興等特 點(diǎn),任何思維和語言都是鞭長莫及的。 尤其是在那“此時(shí)無聲勝有聲”的當(dāng)兒,任何言語都顯得蒼白無力,甚或是多 余的了。語言的細(xì)胞是概念,所以它所能表達(dá)的情意一定是有限的。人們?cè)谑褂谜Z 言的時(shí)候,免不了要加上手勢(shì)和姿態(tài)的動(dòng)作來輔助傳達(dá),以至于有的語言離開了當(dāng) 時(shí)的情景便無法理解了。 外在有形的東西,我們的語言都可以進(jìn)行表達(dá)和交流,而內(nèi)心無形的境界卻是 無法用語言交流的。有些語言,只有本心具有了相同的境界才能夠理解,所以才叫 做會(huì)心之語。比如說,王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shí)”,沒有到了這種境界, 自然理解不了。會(huì)心的人,你舉起一個(gè)指頭,他便能知曉其中的含義;不能會(huì)心的 人,言語說盡了,也還是不得其門而入的。 古人早就辭能不能達(dá)意的問題進(jìn)行過辯論,結(jié)果還是都得承認(rèn)語言文辭有著它 的局限性,“言有盡而意無窮”。而且許多詩詞追求的就是這種境界和效果,比如 那些“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今宵 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mèng)中”以及“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淚眼問花花 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等。 理解不了的候,最好是不去解釋它,而是用心靈去感悟,也許這未盡之意就可 以理解了。一般的人多是由那言語上去了解對(duì)方,可是真正相親相知的人卻用的是 超越了語言的交流,即所謂的“眼波才動(dòng)遭人忌,惟有心頭郎得知”。 至于那些無可稽考的言談,作茶余飯后的笑談可以,使人捧腹解頤,有助于消 化和健康。若是有了心去執(zhí)著,什么事都當(dāng)了真,就難免要徒增煩惱了。比如說那 里見到外星人了,那里有飛碟出現(xiàn)等,還如有什么特異功能穿墻破壁、活了幾千歲 等等的話,聽一聽開開心也就行了。 既然是無稽之談,那么這說者一定要無心,而聽者也一定要無意才對(duì)。結(jié)果, 這說者有心要人相信,聽者或信或不信的。于是,雙方便爭執(zhí)起來,說有說無,不 僅傷了和氣,還破壞了心情和胃口,便劃不來了,而且還要鬧出笑話。人生無處不 是美景,隨他言語周折,我自悠閑自在,方能領(lǐng)略其中的真諦。 |
||||
|
中國社會(huì)出版社
|
||||
|
||||
版權(quán)所有 首都師范大學(xué)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聯(lián)合主辦
Copyright© 2000
北京國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mailto:web@guoxue.com
mailto:web@guoxue.com
![]() mailto:yyyinxl@sohu.com
mailto:yyyinx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