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東 |
|||
|
【 清
】王永彬 原著
馬民書 述論 目 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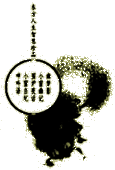 |
|||
|
|
||||
|
|
||||
|
066逾閑與忘世 君子以名教為樂,豈如嵇阮之逾閑; 圣人以悲憫為心,不取沮溺之忘世。 [述論] “嵇阮”是指魏晉間的名士嵇康、阮籍,也可以指以他們二人為首的七位玄學(xué)名士。據(jù) 《晉書·嵇康傳》載: 嵇康字叔夜,……所與神交者,唯陳留阮籍,河內(nèi)山濤。豫其流者,河內(nèi)向秀,沛國 劉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遂為竹林之游,此所謂竹林七賢。 這些人喜好老莊之學(xué),“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發(fā)明奇趣,振起玄風(fēng)”,崇尚自 然,不拘禮法,蔑視名教。他們之所以如此,是與當(dāng)時(shí)的險(xiǎn)象環(huán)生,嚴(yán)法苛政的社會(huì)背景及 個(gè)人的性情相關(guān)相連的,是一種無奈何的心境的體現(xiàn)。 據(jù)史載,阮籍就不允許其子學(xué)他,正好說明了“竹林七賢”的放浪形骸,抨擊名教,飲 酒縱行,是對(duì)那個(gè)不合理的時(shí)代的消極反抗。然而,他們并不像后世的一些所謂的“名士” 那樣,身處太平盛世,卻為沽名釣譽(yù),獲取功名利祿,故作魏晉名士之狀,實(shí)則是“身在江 湖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所謂的隱逸疏放,息影山林,只不過是把它作為竊官盜爵的終南 捷徑而已。 “君子以名教為樂”,真正的讀書人,應(yīng)自覺地遵守軌范,以“齊家、治國、平天下”、 “大濟(jì)蒼生”為己任,刻苦自勵(lì),不斷學(xué)習(xí),探索富國豐民途徑,不以“小我”之小害小利, 而亂“家國”的利益。這樣,才會(huì)有功于社會(huì),有益于個(gè)人,不貪一日之閑,不圖一時(shí)清名, 盡情揮發(fā)自己的專長。即便艱辛、勞苦,也是值得的。 尊“名教”,還必須有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沉醉于名教而不務(wù)世事,只會(huì)陷入清談。 而真正的名教教人入世,教人有所作為。“人皆有惻隱之心”,視民疾民瘼于不見,見國困 家窘而歸隱山水之間,是不可取的。“有惻隱之心”,就應(yīng)有救人于水火的志向。古往今來 的仁人志士,莫不如此。 據(jù)《昨非庵日纂》記載:北宋文學(xué)家范仲淹,少時(shí)貧勤,雖日食齏粥一角,但卻以天下 為己任。據(jù)說,他曾問一相士:“我將來可以做宰相么?”相士答:“否”。他又問:“能 做名醫(yī)否?”相士驚訝地問:“為什么前面的志向高遠(yuǎn),而后面的卑下呢?”范仲淹回答說: “只有這兩樣才可以救人。”由此看來,只要有一份仁人之心,是不會(huì)見傷不扶,見死不救 的。 名教教人以悲憫,悲憫從名教而生光。那些故作風(fēng)流,而踐踏規(guī)范,放任自流的人,是 無悲憫之心可言的。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者,必遭千夫所指,成為孤家寡人;善予人者,人必予之。熱心處世,就會(huì)贏得廣泛的敬愛。 悲憫之心,還有賴于對(duì)名教的精識(shí)。熟于名教,則可辨明是非,判明善惡,疏清美丑。否則, 給惡的、丑的東西以悲憫,則無異于助紂為虐,縱容腐臭。農(nóng)夫與蛇的故事,留給我們的教 訓(xùn),應(yīng)當(dāng)銘記。 |
||||
|
中國社會(huì)出版社
|
||||
|
||||
版權(quán)所有 首都師范大學(xué)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聯(lián)合主辦
Copyright© 2000
北京國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mailto:web@guoxue.com
mailto:web@guoxue.com
![]() mailto:yyyinxl@sohu.com
mailto:yyyinx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