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東 |
|||
|
【 清
】王永彬 原著
馬民書 述論 目 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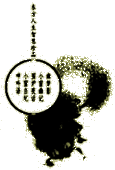 |
|||
|
|
||||
|
|
||||
| 037常人與大家 常人突遭禍患,可決其再興,心動(dòng)于警勵(lì)也; 大家漸及消亡,難期其復(fù)振,勢成于因循也。 [述論]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之旅遇有坎坷,遭到不測,甚至飛來橫禍,亦 當(dāng)是常事常理,關(guān)鍵在于如何對待這些意外變故。所幸的是“常人突遭禍患,可決其再興”。 何也?“心動(dòng)于警勵(lì)也”。為什么正常人突遭禍患可警勵(lì)于心,再?zèng)Q其興呢?根本在于,人們 存不息于心的進(jìn)取之志。甚至不少人“因禍得福”。生活的坎坷,人生的磨難,意外的打擊, 能促使人更加奮發(fā)進(jìn)取,迎難而上。 一方面,挫折的刺激使其“勵(lì)”于心,促使他更加努力,也即“愈挫愈奮”;另一方面, 又使其“警”于行,促使他更加謹(jǐn)慎,選用合適的方法,取得更大的成就。宮刑之辱,使司 馬遷寫出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亡國滅族之災(zāi),使勾踐“臥薪嘗 膽”,“三千越甲終吞吳”。 高位截癱之難,使張海迪奮然與命運(yùn)抗?fàn)帲辛?xí)文學(xué),苦讀外語,專研醫(yī)道,為社會(huì)做出 了應(yīng)有的貢獻(xiàn),創(chuàng)造了豐富的精神財(cái)富,成為時(shí)代的楷模……古者今人不一而足。即使那些 “經(jīng)不起打擊,一蹶不振”的人,也決不是再無興起的可能。實(shí)際上,只要內(nèi)外條件一旦成 熟,他也必然重新振作。可見人的進(jìn)取精神有多么強(qiáng)大的力量,如日月星辰運(yùn)行,生生不息, 永無止境。 但是,為什么“大家漸及消亡,難期其復(fù)振”呢?這是一個(gè)值得深思的問題。一家庭、一 團(tuán)體、一國家日趨衰微,逐漸敗亡,的確是難以挽起的。究其原因,雖然極為深刻復(fù)雜,但 “勢成于因循”卻是最根本的。勢成于因循,就是說在大家都感到十分安全的情況下,對日 益積累的各種弊端、陳規(guī)陋俗,熟視無睹,對已發(fā)生的危機(jī)視而不見,對行將走向滅亡,亦 無所警察。及至家將敗、國將亡,才思興利除弊,企圖逃脫厄運(yùn),但卻已為時(shí)太晚了。 明朝末代皇帝朱由儉,與其他亡國之君相比,不可謂沒有頭腦,不可謂不奮發(fā)圖興。但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明王朝至此,政治黑暗,官場腐敗,民怨沸起,內(nèi)亂外侵已到 無可救藥的地步。縱使他崇禎力行挽起,亦回天無力,劫數(shù)難逃了。 集體安全意識(shí),最易使人形成“天塌下來有人頂,別人能過我也能”的消極思想。眾人皆 墨守成規(guī),承襲陋習(xí),不思改革,如此循環(huán)往復(fù),在無憂無慮、安樂詳和中走向死亡,其真 乃可悲可嘆。 當(dāng)今之人,特別是領(lǐng)導(dǎo)者,得應(yīng)常警勵(lì)于心,樹立憂患意識(shí),警種長嗚。莫待船到江心才 補(bǔ)漏,應(yīng)常審社會(huì)之弊,常察國家之危,不妨跳出“三界之外”,靜觀“蕓蕓眾生”。斷不 可人云亦云,暈暈糊糊,應(yīng)時(shí)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審時(shí)度勢,見微知著,防范未然,及早采 取有力有效措施,使國家社稷有常興生機(jī),趨道昌盛繁榮。 |
||||
|
中國社會(huì)出版社
|
||||
|
||||
版權(quán)所有 首都師范大學(xué)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聯(lián)合主辦
Copyright© 2000
北京國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mailto:web@guoxue.com
mailto:web@guoxue.com
![]() mailto:yyyinxl@sohu.com
mailto:yyyinx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