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東 |
|||
|
【 清
】王永彬 原著
馬民書 述論 目 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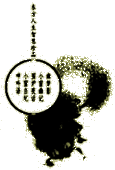 |
|||
|
|
||||
|
|
||||
|
025處事與立言
大丈夫處事,論是非,不論禍福;士君子立言,貴平正,尤貴精詳。 [述論] 大丈夫處事,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是”和“非”,最后堅持的也一定是“是”而非其 “非”,只論“是”、“非”而行事。所謂“是”,乃符合人道天道,利于群體,公眾允 一個人一生要明辯是非、走正道,實不容易。因為,有些奸險小人在與你共事時,只圖 一己的私利,不希望你依正道行事,而希望你按照他最有利可圖的方式做事。否則,他們便 想方設法阻撓你,打擊你。如果你要是趨吉避兇,照著他的意圖行事,就很容易失了正道。 因此,大丈夫行事,但問事情對錯,而不管會不會給自己帶來福禍。古往今來,許多仁人志 士為真理而斗爭,有的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有的卻因此而蒙冤,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 哥白尼因堅持“日心說”,遭到了封建神權統治的迫害,張志新因堅持真理被割斷了喉 嚨。許多無產階級戰士為人類的解放和自由寧死不屈,奮斗終生。他們寧愿把牢底坐穿,寧 愿獻出生命和愛情。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只要是對的,則義無反顧地去做,有勇氣承擔一切禍福,不因此而喪失人格。所 以,大丈夫處事,論是非不論禍福。 著書立說,貴在言辭公允客觀,不可偏私武斷。這是其第一要義。因為,文章是給人看 的。若是觀點有偏差,是非不辯,豈不是誤導了眾人?所以古人云:“文章乃經國之大業”, “文須有益于天下”。“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古之圣賢在論書、詩、賦、 畫時,特別強調行文的格調是否高尚,觀點是否公允客觀。 曹丕認為,文章乃百年大業,一點也不差;而孔子“述而不作”,想必也是有道理的。如 果一篇文章或一本書,語言美麗,包裝很美,而內容偏私武斷、或者有誤人子弟之處,那真 不如不寫。清朝文藝理論家劉熙載在《藝概》中講: 實事求是,因寄所記。一切文字不外此兩種,在賦則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喪 志,其賦亦不可已乎!因此,著作文章一定要客觀公正,謹慎下筆。否則,率爾操觚,哪有什 么可看性呢?正所謂“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言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 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在言辭公允、客觀、平正的基礎上,還須精要詳細,言無不盡。這樣, 才是最可貴的。
所以,大丈夫須不論禍福而處事,士君子要平正精神為立言。
|
||||
|
中國社會出版社
|
||||
|
||||
版權所有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聯合主辦
Copyright© 2000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mailto:web@guoxue.com
mailto:web@guoxue.com
![]() mailto:yyyinxl@sohu.com
mailto:yyyinxl@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