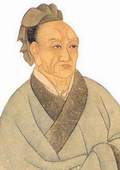
司馬遷
字號:字子長
生卒:前145或前135—前87?
朝代:西漢
籍貫: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一說山西河津)人
簡評:中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尊稱“史圣”
生平簡介
司馬遷自稱其先祖是顓頊時期的天官。《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后,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時期,司馬遷的祖上來到秦國。他的直系祖先是戰國時期秦國著名的武將司馬錯。秦惠文王時期,司馬錯曾經在朝堂上與張儀辯論,辯論內容被收入《戰國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觀止》,名為《司馬錯論伐蜀》。辯論勝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馬錯等人出兵巴蜀,得勝而守之。六世祖司馬靳為名將武安君白起副手,參與長平之戰,坑殺趙卒四十萬人,司馬錯、司馬靳等軍事之功為秦國奠定了一統天下的軍事基礎。
司馬遷的父親是西漢武帝時期太史令司馬談。司馬談是當時一位非常杰出的學者,著有《論六家要旨》一文,系統總結了春秋戰國秦至漢初以來陰陽、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對道家思想進行了高度肯定。該文是對春秋戰國以來的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練總結。
司馬談在約漢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間任太史令。公元前145年,司馬遷出生于家鄉夏陽(今陜西省韓城市)。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司馬遷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遷在“山環水帶,嵌鑲蜿蜒”(《韓城縣志序》)的自然環境里成長,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氣所陶冶,又對民間生活有一定體驗。10歲,司馬遷隨父親至京師長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國學習;家學淵源既深,復從名師受業,啟發誘導,獲益不淺。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里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司馬遷大約22歲開始外出游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回到長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職責是守衛宮殿門戶,管理車騎,隨從皇帝出行。他隨漢武帝到過平涼、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過當時最南邊的昆明。司馬遷在讀萬卷書的基礎上,開始行萬里路,司馬談要求他兒子來進行一次為期兩年多的全國漫游。司馬遷從20歲開始的全國漫游,是為寫《史記》做準備的一次實地考察,他親自采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保證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他這個漫游,也是《史記》實錄精神的一種具體體現。
此外他遍歷名山大川,飽覽了祖國山河的壯美,陶冶了性情,從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學的表現力。所以說司馬遷的這次漫游,正是司馬遷走向成功的極為堅實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漢武帝舉行大規模的巡行封禪,步騎十八萬,旌旗千余里,浩浩蕩蕩。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史官,司馬談這時候卻病了,經過漢武帝的允許留在洛陽養病,正好司馬遷從長安匆匆趕去追隨漢武帝,在洛陽見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親司馬談。
司馬遷在為《史記》寫的“自序”里,詳細記錄了司馬談在“河、洛之間”對他說的那番語重心長的遺囑。司馬談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司馬遷俯首流涕,對父親發誓說:“我雖不聰敏,請容許我把您已記錄編排過的有關過去的傳聞,完整地書寫出來,絕不敢有缺漏。”洛陽相會,就這樣成為這一對鐘情于歷史學的父子之間的生死之別。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后,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志(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定立了“太初歷”,該歷法改變了秦代使用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的習慣,而改以正月為歲首。從而,為中國的農耕社會奠定了其后兩千年來所尊奉的歷法基礎。之后司馬遷便潛心修史,專心寫作,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主動請纓出擊匈奴,兵敗被俘,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叛降,全家當誅。而在這時,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卻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兵敗投降是因為“矢盡道窮,救兵不至”,而且李陵是希望“欲得其當而報漢”。李陵雖然兵敗,但是他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司馬遷這番表述卻沒有得到漢武帝的理解。漢武帝認為他是藉李陵之功,詆毀這場戰爭的主帥李廣利(此人為漢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進而批評自己用人不當,造成軍事失利。漢武帝因而大怒,將司馬遷投入牢獄,以“誣罔”(欺騙皇帝)的罪名判處死刑。當時的死刑有兩種方式可以充抵,第一種是“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另一種是按照漢景帝時期所頒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許之”,處以腐刑(閹割)。由于沒有足夠的金錢可以贖身,司馬遷只得屈辱地接受腐刑。對此他曾表示過“禍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詬莫大于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出獄后,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后世稱《太史公書》為《史記》。
“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后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后,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后世。
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成就了《史記》——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后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對后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并稱為史學“雙璧”。因此司馬遷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史圣。與司馬光并稱“史界兩司馬”,與司馬相如合稱“文章西漢兩司馬”。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均已散失,唯《藝文類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賦》的片段和有名的《報任安書》(即《報任少卿書》)。《報任安書》表白了他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決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賦》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