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憂無悔的終生選擇——美國杰出漢學家倪豪士
——海外當代漢學家見知錄之四
倪豪士(WilliamH.Nienhauser,Jr.),1943年生,1968年畢業于印第安那大學,獲碩士學位,1972年在該校獲博士學位。曾任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現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文學系霍爾斯特·斯科姆講座教授。先后兼任臺灣大學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學研究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等。倪豪士專門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尤其是唐代文學研究,著有《皮日休》、《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柳宗元》(合著)及近百篇論文與書評。編有《唐代文學研究西文論著目錄》、《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等。學術研究之外,并致力于《史記》、杜詩、唐傳奇、《搜神記》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他還是美國惟一一份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雜志《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i.e. CLEAR)的創立者,并長期擔任主編(1979-2010)。2003年倪豪士由于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突出貢獻,獲得Humboldt Foundation終身成就獎。
一、漢語經歷
據倪豪士本人介紹:他對中國的興趣產生于高中時期:“我直到十六歲才見到過一個中國人。我在高中時熱衷于學歷史,讀了很多傳記與傳記文學。有一本書敘述了一個美國船長如何在十八世紀初和滿清政府做生意,另一本書描述了二十世紀前半葉駐華的幾位美國軍人。在這兩本書里可以看到,中美這兩個國家及兩國人民,雖然不一樣的地方很多,但是還有不少地方雙方可以彼此了解,彼此尊重。就這樣我慢慢對中國產生了興趣。”(見徐公持《一生一世的賞心樂事:美國學者倪豪士教授專訪》,文學遺產2002年1期,下同)中學畢業以后,倪豪士就讀于一所科技大學。這個大學是他父親選擇的,他希望倪豪士將來成為一個工程師。“可是,我不知道念大學是不是我要走的路。因此,我念得不太努力,成績也不太好。有一天我在電視里看到一個面向中學畢業生做的陸軍征兵廣告。就這樣,1961年12月中,我當了兵,并且順利進人了陸軍語言學校”。在陸軍語言學校,倪豪士又面臨兩難選擇:是選俄文或是選中文。一方面,他非常喜歡俄國十九世紀的長篇小說作家:“如果學會了俄文,就可不必借助翻譯就可以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原著;但另一方面,學中文可以滿足他對中國歷史的興趣。斟酌再三,還是選了中文”。倪豪士說:“此后我也一直沒有后悔”。
陸軍語言學校一年的中文課程給倪豪士打下了中文基礎,并使他不斷增添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三年兵役退伍后,倪豪士于1965年進人印第安那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專修中國文學。大學期間,他開始接觸歐洲和日本的漢學研究成果,并學會了利用大量參考書細讀古典作品的方法。當時倪豪士的中國文學指導教師是柳亞子之子柳無忌。在柳先生指導下,倪豪士決定重點研究唐代文學,并于1968年請假一年去德國波恩大學進修。當時德國漢學是專門研究古典文學的,波恩大學的教授對唐代文學更為重視。他們指導倪豪士用沒有標點過的版本,并參考日本學者的注釋和研究成果來攻讀唐代文學。1969年回到印第安那大學后,倪豪士請柳無忌先生開一門“柳宗元研究”課程。后來他把其中的研究課題所寫的論文編輯整理,寫成一本專著《柳宗元》于1973年出版。在此同時也完成了博士論文《(西京雜記)中的文學和歷史》。
拿到博士學位后,倪豪士赴威斯康星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倪豪士后來回憶說:我原來以為已經是中國文學博士,中文已經不是問題。到威斯康星之后我馬上發現這個看法是不對的。我教的第一門課是中國文學史。我一進教室的門,就看到里面有八個研究生,坐在前面的四位是剛從臺灣大學畢業的中國學生。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很多關于中國文學的發展情況,所以我必須每個晚上再三琢磨第二天的講課提綱,只能用這個辦法才能避免學生問我太多我不能回答的問題。但無論我怎樣努力,不時還有人指出我寫錯的字或說錯的話。到了這個時候我才算真正了解一句有名的中國諺語:“活到老,學到老,還有三分學不到。”
1975一1976年倪豪士得到一筆獎學金,又去德國漢堡大學跟柳茅彩教授學習西方和中國的中古敘述文。其間他發表了兩篇論文:《解讀韓愈〈毛穎傳〉中的諷喻》(《遠東》1976年12月),《試析〈文苑英華〉中“傳”的結構》(《亞洲研究季刊》,1977年5月)。1976年我回到威斯康星大學繼續研究中國的中古小說和詩歌。1979年出版了專著《皮日休》。在這期間還發表了幾篇討論六朝、唐代和明清文言小說的論文。1980一1983年倪豪士擔任威大東亞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在此期間編寫了《印第安那中國古典文學指南》,并用中文發表了《中國小說的起源》、《南柯太守傳,永州八記與唐代傳記及古文運動的關系》等一些學術論文。
1983年,他應邀擔任臺灣大學外文系客座教授。倪豪士認為這是他第二次深入學習中文的機會。他深入到臺灣大學的同事和同學中,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和學習漢語。這一年他已年屆不惑。1985年他又去了臺灣,一面在臺大外文系教書,一面在斯坦福中心學習正規的中文課。因為臺灣的本地人都喜歡說閩南話,所以我也學了一學期的閩南方言。他認為:學習南方的方言能使他更多地了解古代漢語的發音
從1989年起,倪豪士專注于對《史記》的研究和翻譯,同時也進行唐傳奇方面的研究。進入新世紀后,倪豪士與大陸的學術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有了更多的接觸。新世紀剛開始的2001年,他就接受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的邀請,擔任客座研究員;接受《文學遺產》的專訪,介紹他學習、熱愛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學的經歷,他的治學方法和體會,他對翻譯中國古典文學的見解和做法等。2003年7月,他參加兩岸學者共同參加的在臺北淡江大學召開的紀念杜甫誕生12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介紹了美國學者研究杜甫的成果和特點;2009年3月,赴上海參加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哈佛大學東亞系合作舉辦的“都市繁華:1500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會上發表《我心中的長安:解讀盧照鄰〈長安古意〉》學術論文;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發表《重申李娃傳》的學術講演。2010年6月16日(端午節),他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中華詩詞青年峰會”上,作為外國詩人代表,為“前十強”頒獎。
這一切,正像倪豪士自己所說的,他把學習中文、走進中國,當成一生一世的賞心樂事;對一輩子追求、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也是傾心盡力、無憂無悔!
二、研究成果
他的主要論著有《皮日休》、《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柳宗元》、《印第安納中國古典文學指南》。編著有《唐代文學研究西文論著目錄》、《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以及《中國小說的起源》、《南柯太守傳的語言,用典和言外意義》、《碑志文列傳和傳記:以歐陽詹為例》、《美國杜甫研究評述》、《我心中的長安:解讀盧照鄰〈長安古意〉》、《重審李娃傳》等近百篇以唐代文學為主的學術論文與書評。
倪豪士的學術研究有一個宏大的學術視野和寬厚的學術基礎。《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1995由臺北南天書局出版,中華書局2007年再版。該書收錄了作者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撰寫的十二篇學術論文,專論唐代文學尤其是唐代小說。其中像《略論九世紀末中國古典小說與社會》、《〈南柯太守傳〉、〈永州八記〉與唐傳奇古文運動的關系》、《柳宗元的〈逐畢方文〉與西方類似的比較研究》等篇皆糅合文史、兼及中外或社會政治,可看出其學術視野的寬闊;《〈南柯太守傳〉的語言、用典和外延意義》、《略論碑志文、史傳文和雜史傳記:以歐陽詹的傳記為例》等涉及多種文體和學科類別,可見其學術基礎的寬厚。在《中國詩、美國詩及其讀者》中,談到西方讀者接受包括李白、杜甫在內的中國古典詩歌的困難:一是不明白中國古典詩歌中典故和形式,及在其詩歌里的重要性;二是中國古代人與我們現代人的看法、希望及道德觀有差異;三是翻譯家有各種不同風格,雖然他們都努力地嘗試譯好中國詩,但是西方讀者還是常常分辨不出杜甫和李白的不同詩風。這好像是不經意的閑談,實際上亦出于大量資料的分析占有和深入思考:他在2003年于臺北淡江大學召開的“杜甫與唐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有個學術報告《美國杜甫研究評述》。其中對以洪葉《杜甫研究》(1952)為發端標志,到宇文所安、周珊珊二十世紀末的學術新著,不僅逐一梳理、評點,也指出在周著中對杜甫的道德觀念不理解和不認同。可見他在《中國詩、美國詩及其讀者》的觀點是建立在大量資料的分析占有之上的,有著寬厚的學術視野和學術根基。備受學界稱贊的《史記》英譯本更是如此。該書以文獻學的豐厚而著稱:全書不但附有西文和日文譯本書目、中外研究成果等學術資料。每卷譯本的后面還附有全書的參考文獻目錄,包括中外文的《史記》版本研究、參考文獻、譯本、歷代注疏、關于《史記》及司馬遷的研究、《史記》及《漢書》的比較、其他中文、日文和西文著作等,還包括漢語拼音、漢字及官職英文譯文的索引、春秋戰國圖、秦帝國圖等。他在1970年就開始《史記》的研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次學術會上還專門做過“百年來的《史記》研究”學術報告。到九十年代才開始翻譯《史記》,可見學術基礎的豐厚。
倪豪士在漢學研究中善于思考,且目光精到。如學界對唐人傳奇《李娃傳》的研究由來已久,但對其成書時間和人物原型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倪豪士在考辨基礎上對其寫作時間提出兩個假設:第一,白行簡不一定是在一年之內完成《李娃傳》的創作。他聽“一枝花”的故事以后,可能向親戚朋友詢問此事細節,“傳”之創作可能長達十幾年;第二,如果白行簡寫《李娃傳》是別有用心,在以前學者提出的猜想之外,還可以考慮鄭穆和鄭亞分別為滎陽公和滎陽公子。如果《李娃傳》是影射鄭亞的話, 白行簡寫成《李娃傳》當在長慶二年或三年前后。這個判斷不僅有文獻學方面的分析,更出于他對傳奇小說的產生原因的思考,其中又對中外各家之說的分析比較。他在上述的訪談中,也曾談到他對小說起源的看法。他認為:小說應該是在民間口傳故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像《左傳》“鄭伯克段于鄂”和《史記·高祖本紀》中“高祖為亭長時”的那些故事都是很好的例子。魯迅以為在唐代“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中國小說史略》),但是,傳奇雖然是有意為之的,傳奇作者的寫作目的也并不相同。卞孝萱的《唐代文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杜德橋的《李娃傳的研究.校勘及英譯》(倫敦:牛津出版社,1983年)都已經提出唐代小說和政治的關系。所以雖然《李娃傳》文學價值相當大,但創作目的則是為了政治攻擊,和韓愈、柳宗元之寫“傳”情況相似。至于唐代作者對講故事的態度及寫作方法怎么樣發展,可以看一看沈亞之的文集。沈年輕時簡單地把別人告訴他的故事記下來(如《移佛記》),發展到在其寫作成熟期在《馮燕傳》或者(秦夢記》中加人自己的創作。因此,小說大概在很早的時候起源于民間文學。在戰國時代之后,不時出現于文人作品,直到唐代才正式成為文學作品。倪豪士由此出發,認為西方漢學界最需要的是一本像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陳注:王夢鷗,臺灣政治大學教授,現代唐人小說研究發軔者之一,出版四卷本《唐人小說研究》)那樣有詳盡注解的唐傳奇英譯本。本校有計劃在今后兩三年內出版這樣一部翻譯集。所以表面上看來,僅僅是一篇小說寫作時間的推斷,實際上是厚積薄發,源于對唐人小說乃至古代小說產生原因和研究方向的長期思考。
倪豪士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的另一巨大貢獻是在《史記》翻譯上。1961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華茲生英譯的兩卷本《史記》譯本。主要是《史記》中漢代部分的“列傳”,因此又名《史記:漢朝》。1993年,華茲生又出版修訂本,并增加新譯的《史記:秦朝》。華茲生的《史記》譯本,主要以普通讀者為對象,關注的是《史記》的文學性,故選譯的多是能體現《史記》文學風采的“列傳”、“世家”。翻譯也采用自由性翻譯并盡可能少用注釋,以使譯文流暢具有可讀性。倪豪士從1970年代就開始從事《史記》研究,有感于到20世紀80年代末,《史記》中仍有相當一部分沒有令人滿意的完整西文譯本,于是與鄭再發、Robert Reynolds、陳照明、呂宗力等組成翻譯團體,從1991年起開始翻譯《史記》。他們意識到《史記》應該被完整閱讀,沒有完整的翻譯將誤導西方讀者。要譯出一種忠實的、具有詳細注解并盡可能具有文學性和流暢性的《史記》全譯本。按照計劃,工作完成時,整部《史記》的英譯本將達到9卷。到目前為止,他們已先后出版了《史記·漢以前的本紀》(1995)、《史記·漢以前的列傳》(1995)、《史記·漢本紀》(2002)、《史記·漢以前的世家(上)》(2006)、《史記·漢代的列傳(上)》(2008)等五卷。譯本保留了《史記》本紀、世家、列傳等的排列順序,內容包括“序言、使用說明、紀年說明、度量衡對照表、縮寫表、譯文”幾個部分;譯文的頁下,附有詳盡的歧義考證、地點考證、相關章節成書說明、互文考證說明、文化背景知識注釋及資料依據、詞匯對照表等;在每章譯文后面,附有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的相關評注和說明、以及西文和日文譯本書目、關于該卷的中外研究成果等。可以說是到目前為止,是西方最完備、也最富有學術價值的《史記》譯本。因此,該譯本一出版,就受到西方學者的紛紛稱譽:卜德認為是“漢學的一項偉大成就”;加里·阿巴克爾(Gary Arbuckle)亦認為“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并對各領域的讀者都將有幫助”;張磊夫(Rafe de Crespigny)稱贊“翻譯是可靠的,注釋是清晰而有幫助的……譯著將使更多英語世界讀者感知《史記》的學術性……通過這些著作,西方的學術界和文學界將對早期中國的輝煌和浪漫有更多了解,并對由偉大史家所展現出來的人類教訓有更好理解” ;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在對比華茲生的《史記》譯本后評價倪豪士領銜英譯的《史記》說:“從文學視角來看,華茲生生動的譯本作為愉悅和悠閑閱讀至今仍無人超越…..但華茲生按照年代編排他的翻譯時,他歪曲了司馬遷的原始構想,讀者將不能察覺司馬遷結構的意義。與之相對照,倪豪士保留了《史記》的形式,允許讀者盡可能猜想司馬遷編撰的決心…..倪的譯注在朝著盡可能使英語讀者理解司馬遷所要求讀者具有的這種留意、批判解釋的漫長道路前行。我對華茲生的翻譯保有一種親密感,我仍舊欣賞。但是我認為倪的譯著將更為值得仔細反復閱讀。如果他和他的團隊能夠一直堅持到終點,他的翻譯將是一個世紀以來或更長時間里最終的英譯本”。
倪豪士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貢獻還有他主編的《中國文學》雜志。鑒于大部分研究中國的雜志都在東岸,而且沒有一份雜志專門探討中國文學。他在1979年與歐陽貞一起創辦了這份總部設在中西部的專門研究中國文學尤其是古典文學的雜志。雜志剛開辦時還需要資助,但由于陸續刊登了一批有分量的論文、書評及學術討論,學術影響逐漸擴大,訂戶逐漸增多。現在刊物基本上已能通過收取訂閱費而達到經濟自理。這在學術刊物尤其是國外以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為重點的學術刊物中是不多見的。
三、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
作為海外漢學家,倪豪士的著作顯示了與中國大陸學者不同的、獨特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如:《〈文苑英華〉中“傳”的結構研究》一文中,采用結構主義理論進行分析,將《文苑英華》中的“傳”分為三種類型;《唐人載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別雙重標準初探》一文則采用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視角對唐人小說及相關文獻中的女性形象與性別雙重標準進行解析。在整部書中,作者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盡可能選擇合適的理論方法進行解讀,得出的結論還是令人信服的。在《中國小說的起源》一文中,作者又采用比較研究:比較了中國小說概念中的“傳、說、奇”和西方傳統中的文化劃分——模擬、教誨和娛樂的同異,從而把周朝作品,如《莊子》、《孟子》、《戰國策》、《國語》等列入小說史的考察范圍。《柳宗元的<逐畢方文>與西方類似物的比較研究》也是一篇典型的比較文學研究。這些研究方法,可以豐富我們對于中國文學現象作更多層面的理解和思考。這正可以借用蘇軾的詩來形容: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倪豪士研究中國傳統文學這種獨特視角和方法的產生原因,一方面是出于西方漢學家的共性:按照西方現代的觀點,閱讀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投射,也就是批評將文學作品視為經驗的記錄;二是評論,與文本習習相關去了解文本任何一部分;三是詮釋,對作品進行整體性的關照。相對來講,傳統的中國文學理論較接近于投射理論,而西方則中傾向于評論方式。近些年來,又強調詮釋理論,刻意尋求第二層涵意。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對中國文化的深層和理性思考:他在接受徐公持的訪談中曾談到中美之間在文化認知上的差異:作為一個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文化指的是存在于日常生活、宗教及藝術遺產中的某種傳統。但對于中國人來說,“文化”實際上一種可以界定為種族的東西。中國人之間對五千年文化有著認知上的相似性。做一個中國人就是要以一種特定的方式生活、行動、飲食、談話,那些有中國血統并分享這一文化的人就是中國人。而大多數美國人卻達不到這一點(猶太人的社區是一個例外,他們的文化認同方式與中國人很接近)。鑒于這種認識,他感到年輕時想成為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的念頭并不現實,從而開始尋找一種能適合作為一個美國人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與歷史的途徑。其中“文學的文化研究”就是他探尋的主要研究方法。上述的《〈文苑英華〉中“傳”的結構研究》、《唐人載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別雙重標準初探》、《柳宗元的<逐畢方文>與西方類似物的比較研究》等皆是其研究方法的嘗試。當然,進行這類思考,采用這種研究方式的在美國也不只是倪豪士,葉舒憲教授《高唐神女與維納斯》,已故的柏克利大學薛愛華教授一些著作也都采用了類似的研究方法。
倪豪士教授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還有一點值得我們借鑒,就是用現代的眼光、現實的需要來進行規劃,確定選題。如針對前面談到的西方讀者接受包括李白、杜甫在內的中國古典詩歌的困難,他考慮一個“能讓西方讀者欣賞中國詩歌的方法”,那就是:“把原詩逐字譯成英語,然后再解釋那首詩的構造、語言(包括用典)和技巧,最后給一個比較自由的文學性翻譯”。這個方法的前提是要有充足的原詩外文譯本。從此出發,他開始著手號召通過互聯網進行這方面的翻譯工作:“本人希望所謂的‘電子文本’會讓東西方學者有機會從互文文本的角度,重新審視一些有名的詩文”。他本人就打算用“電子文本”來斷定《下邳侯革華傳》是不是韓愈的作品,以及研究柳宗元的一些反映民間文化的“記”,如《道州毀鼻亭神記》等。
倪豪士最近從事的大規模的《史記》翻譯也是從中西方文化溝通的現實需要。如上所述,西方至今沒有一個完整的《史記》譯本。那種只注意故事性和行文流暢生動的節譯方式,將會誤導西方讀者。從而用二十多年時間,譯出一種忠實的、具有詳細注解并盡可能具有文學性和流暢性的《史記》全譯本。除了《史記》之外,他還打算出版一本唐傳奇的英文翻譯集。也都是出于對中國文學的熱愛,出于溝通中西文化的強烈使命感。
倪豪士主要學術著作目錄
專著:
1、《柳宗元》,紐約特維恩出版社,1973
2、《皮日休》,波士頓特維恩出版社,1979
3、《印度安納中國古典文學指南》,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1986
4、《唐代文學研究西文論著目錄》,臺北·漢學研究中心編印,1988
5、《史記》(英文翻譯)第一、二、三、四、五冊,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1994、2002、2006、2008
6、《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臺北南天書局,1995
7、《印第安那中國古典文學指南》第二冊,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1998。
8、《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論文:(近百篇)
1、博士論文:《〈西京雜記〉中的文學和歷史》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1973。
2、《中國小說的起源》臺北·學生書局《古典文學》,1985年8月
3、《南柯太守傳,永州八記與唐代傳記及古文運動的關系》(臺灣大學《中外文學》,1987年)
4、南柯太守傳的語言,用典和言外意義》(《中外文學》,1988年,54一79頁)
5、《碑志文列傳和傳記:以歐陽詹為例》(《第一屆國際唐代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
6、《讀范仲淹唐狄梁公碑》(《紀念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建會,1989年)
7、《柳宗元的逐畢方文與西方類似的比較研究》(《唐代文學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
8、《美國杜甫研究評述》(《杜甫與唐詩學》臺北·里仁書局2003)
9、《我心中的長安:解讀盧照鄰〈長安古意〉》“都市繁華:1500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2009年3月
10、《重申李娃傳》,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發表學術講演,2009.3。
11、《陶潛與〈列子〉:四世紀詩歌中的互文性及其影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及中華語言文化中心講演,2011年2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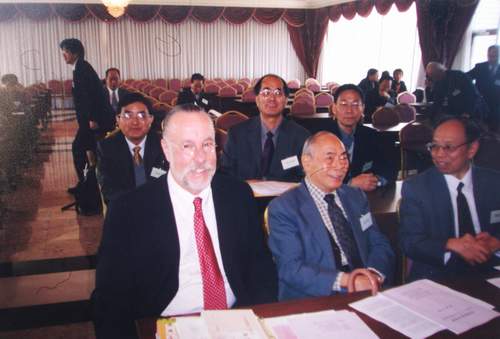
2003年6月,倪豪士(左一)在臺灣淡江大學《杜甫與唐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 (陳友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