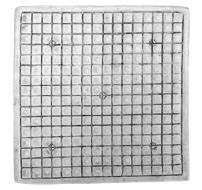圍棋盤路數的奧妙
圍棋盤的路數,今天我們熟悉的是十九路,也就是縱橫各十九道。在遠古的歷史中,它曾經歷過十三路、十七路的前身;在不可知的未來,現行的十九路會不會再次擴大,變為二十一路?這種可能性無法斷然否定。那么,棋盤的路數由少到多,由簡到繁,其中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漢代彩繪灰陶圍棋俑(距今2100年)
圍棋盤的路數多少,從古到今是有一個演變的過程。今天我們熟悉的是十九路,也就是縱橫各十九道。在遠古的歷史中,它曾經歷過十三路、十五路、十七路的遞增;在不可知的未來,現行的十九路會不會再次擴大,變為二十一路?因為未來不能確知,這種可能性也無法斷然否定。那么,棋盤的路數由少到多,由簡到繁,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又有著怎樣的意義呢?
說到圍棋盤的路數,不能不從圍棋的起源說起。也即,圍棋盤最初的樣子是怎樣的,有多少道盤線。圍棋的起源,一說是源自于“易”。如果此說成立,則在原始的符號記事時代,人們劃地為盤,折枝為子,以此推卦演易,那么“萬物之數,從一而起”(《棋經十三篇》),一生二,二生三,“三”為一爻,由此可推演萬物之變化。于是,三路便是棋盤的最基本路數。
圍棋源于易,則圍棋最初是作為占卜的工具,而非爭勝負的游戲甚至技藝。如果從能夠爭勝負的角度來說,極簡單的路數便不能滿足了。棋盤上的棋子,其生存條件是氣,縱橫三格,正好中間留一“氣”;即所謂有了一個“眼位”。五格成兩眼,在五路盤上,無爭執的話,雙方均可安然活出一塊棋。但一方先行,往正中心落子,正好雄踞各方均為“三三”的位置。另一方再下子,絕無生路。七路盤,正中心位置為“四四”,即現在所謂的星位。如先行一方占“四四”,另一方可從任一角潛入“三三”,所以行棋雙方一般都會各占兩個“三三”,先自固,再求發展。所以,理論上,圍棋盤用來爭勝負,最少應為七路。
但七路盤變化太少,缺少爭棋的趣味性。而九路盤變化大為增加,先行一方雖絕對有利,但后手方并非毫無機會。前幾手占三三還是其它位置,也有了選擇余地。即使實行對角三三的座子制,也并非不可下。直到現在,初學圍棋者還往往從九路盤開始學起;職業棋手間,還舉辦過帶有實驗性質的九路盤比賽,殺得難解難分。雖無文字和實物佐證,在圍棋的演變過程中,流行過九路盤,應是大有可能的。
考古文物的佐證
珍罕的十七路隋青釉棋盤(距今1500年)
中國最古的圍棋盤大致可以從原始氏族社會的一些彩陶藝術圖案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在原始社會末期的陶器上,一些圖案被考古專家稱為棋盤紋圖案,線條勻稱,格子整齊,頗似現代的圍棋盤。如陜西西安半坡出土的原始社會彩陶罐上,繪有縱橫十至十三路類似圍棋盤的圖案。
現存有實物發現的路數最少的棋盤是十三路盤。1977年,在蒙古敖漢旗豐收公社白塔子大隊發現一座遼代古墓,墓內供桌下,有一高10厘米、邊長40厘米的圍棋方桌,桌上畫有縱橫十三路的圍棋局。
而已知最早的圍棋盤實物出自西漢。咸陽西漢中晚期甲M6墓葬出土石棋盤一件,長66.4厘米,厚32厘米,四角的鐵足高48厘米。棋盤面磨制光滑,周飾一回H方連續菱形方格紋,其中以黑線畫出棋格15*15共225格;四鐵足呈不規則圓形,位于棋盤面的四角;背面未經打磨,留有鑿痕。
1971年,在湖南湘陰發現一座唐代古墓,墓內隨葬品中有一青瓷圍棋盤。正方形,邊長55厘米,縱橫十五路,四邊刻有圓弧形裝飾,上敷黃油。十五路棋盤從漢代一直延續到唐代(甚至遼代還有十三道棋盤),而唐代、遼代的十五、十三路盤,早已不是當時的通行的棋局,而可能是漢代或更早流行的制式。這一方面說明當時由于交通的不便,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限制,在一些邊緣地區仍在流行著“古制”,或人們出于崇古或簡便易學的需要,有意識地保留了古代圍棋的制式;另一方面,則說明任何制式的圍棋,其產生、流傳、演變,都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導致同一時代,可能多種制式的圍棋和平共處。
這種情況也適用于對十七、十九路盤的考察。1954年,在河北望都發掘的東漢古墓中發現一石棋局,高14厘米,邊長69厘米(馬融《圍棋賦》謂“三尺之局兮,為戰斗場”,漢時一尺約合23.5-24厘米),上刻有縱橫十七道線。三國時魏邯鄲淳《藝經》說“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1975年,山東鄒縣發掘的西晉劉寶墓中,有一副裝在灰色陶盒里的完整的圍棋,黑白共289子,充分說明十七路盤還是這時的通行制式。劉寶官至侍中,安北大將軍,卒于永康二年(301年)。
南朝宋時有一首《讀曲歌》:“坐倚無精魂,使我生百慮。方局十七道,期會是何處?”讀曲歌是南朝宋時流行于江南一帶的民間歌謠,它說明十七路盤還通行于民間。
1972年,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娜唐墓中,出土了一幅絹畫,叫“圍棋仕女圖”,圖中所繪棋盤為十七乘十六道(十六當為十七之誤)。該墓墓主是武則天時安西都護官員,它說明初盛唐時,十七路盤仍在邊遠地區使用。而直到現在,藏棋、錫金圍棋猶流行十七路制。
十九路盤源自何時
那么,十九路盤起于何時,卻成了一道難題。一說在三國時期已流行,理由是北宋棋待詔李逸民《忘憂清樂集》中,收有“孫策詔呂范弈棋局面”,該圖譜就是十九路的。另外,還有“晉武帝詔王武子弈棋局”,也是十九路的。一種觀點認為,《忘憂清樂集》有宋刻本,其發現和流傳經過十分清楚。宋人著書刻書一般比較謹嚴,該書所收圖譜當有所本。另外,有三國邯鄲淳《藝經》所記、有南朝《讀曲歌》所詠的情況下,作為棋待詔的李逸民不可能自己作偽,也不可能不辨不查便掇拾前人偽譜于集中,而蒙蔽宋徽宗和世人。從這個情況看,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時期,十九路圍棋和十七路圍棋都在流行。三國時期,十七路圍棋主要流行于北方,十九路圍棋主要流行于南方,特別是吳國的宮廷中。到兩晉時期及其以后,十九路圍棋也開始在北方流行開來。
一般認為,十九路盤至少在南北朝時開始流行。成書于北周的敦煌寫本《棋經》,《像名篇》中有“棋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數”之說。“三百一十六”應為“三百六十一”之誤,“放”應為“仿”。十九路棋局出現在棋經中,說明北周時十九道棋盤成了主要對局用具。
此外,中國古代數學名著《孫子算經》有一道算題:“今有棋局方一十九道,問用棋幾何?答曰:‘三百六十一。’術曰:‘置一十九道,自相乘之,即得。’”《中國圍棋》有一注釋曰:《孫子算經》:見《隋書經籍志》,不著撰人姓氏,原作者究為何人,諸家說法不一。清朱彝尊認為春秋時孫武所作;戴震訂為東漢明帝以后著述;阮元考證作者當為漢以后人。其書久已失傳,清乾隆時,閣臣從明《永樂大典》中輯出,始得殘本,但正文與注文,多已混合,不可復辨。《唐書·藝文志》載:李淳風注甄鸞《孫子算經》三卷。甄鸞,北周時人。李淳風,初唐時人。正文“三百六十一”句以上,當系原文。“術曰”以下數語,或為注文。果如斯,則原文最低限度亦當為北周時人語,上至漢魏的可能性也不能絕對排除。
一種圍棋制式從產生到流行,總有一個發展過程,如果孫策棋譜不確,十九路盤至少在南北朝前期時已產生,應屬不謬。已發現的十九路盤的最早實物是在河南安陽隋代張盛墓中出土的一具瓷棋局。唐人裴說《棋》中有“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崄巇”的詩句。《忘憂清樂集》中所收棋譜,也都是十九路的。說明十九路盤在唐代已成為標準制式。
與路數相關的變化與子力價值
棋盤的演變過程,有一個逐漸由簡單到復雜的軌跡。棋盤越大,變化就越多,棋勢越復雜,斗智的趣味性也更濃。關于圍棋的變化,唐朝馮贄在《云仙雜記》中感嘆:“人能盡數天星,則通知棋勢”。十九路盤已是如此,那么今后棋盤的路數有沒有再增加的可能?
有人曾作過計算,在十七路盤上下棋,圍三路共需48子,圍出112目,平均每子的價值為2.33目,圍四路需40子,圍出81目,每子價值為2.03目,子效差值為0.30目,三路有利:十九路盤,圍三路56子,136目,平均2.43目,圍四路48子,121目,平均2.65目,子效差為0.22目,四路有利;而假如棋盤增加到二十一路,圍三路需68子,圍出152目,平均2.24目,圍四路需56子,169目,平均3.02目,子效差為0.78目,圍四路絕對有利。據此斷言,十九路盤是最佳路數,因為它在三、四路間落子,其子效差最為接近,在守地與取勢之間最為均衡。
但是,在二十一路盤中,雙方肯定都不會去占三路,除星位外,還可能選擇目外、高目、超高目、五五之類的著點。二十一路盤圍五路需44子,圍出121目,平均2.75目,雖不如四路,但子效差僅為0.27目,接近于十九路盤的四、三路子效差。由此二十一路盤在理論上并非沒有可行性。
十九路盤己流傳了1500年以上,隨著人們對圍棋的理解的進一步加深,掌握得越來越熟練,也許在不遠的將來就會出現二十一路的棋盤。即使現在不可能,至少,現代人可以去感受一下在二十一路盤上下棋的滋味。不說作為創新的一種嘗試,即使單純從提高棋藝的角度說,二十一路棋盤中,棋更為復雜、多變,如果通過理論研究與實戰,有了一些心得,回過頭來,也可以加深對十九路盤的理解,提高駕馭棋局的能力。這就像下慣了十九路盤,再去下十七路盤,你會覺得簡單得多一樣。既然現代棋手可以進行九路盤的趣味比賽,為什么不能在二十一路盤上試一試呢?能從中發現圍棋的更多的奧妙,亦未可知。
刊于《國學周刊》第53期第3版(2014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