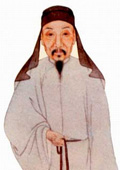
顧炎武
字號:原名絳明亡,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
生卒:公元1613年~1682年
朝代:清初
籍貫:江蘇昆山
評價:清學“開山始祖”,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顧炎武出身于江東望族,明末家道中落。幼年承祖父命出繼堂叔為子,嗣母王氏,十六歲未婚守節,撫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邊黑,性情耿介,不諧于俗,唯與同里歸莊(玄恭)為摯友,時有“歸奇顧怪”之謂。
少時深受嗣祖顧紹芾的影響,關心現實民生,注重經世學問。十四歲取得諸生資格后,便與歸莊共入復社,與復社名士縱論天下大事,反對宦官擅權。二十七歲鄉試落第后,他“感四國之多慮,恥經生之寡術”(《亭林文集》卷六),斷然棄絕科舉之道,發憤鉆研經世之學,遍覽歷代史乘、郡縣志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全國各地山川、地理、農田、水利、兵防、物產、賦稅、交通等資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
書未成而明亡,清兵南下,昆山城破,嗣母王氏絕食二十六日,慷慨殉國,遺命勿仕清廷。顧炎武深受感動,與歸莊等人以匡復故明為志,積極投入蘇州、昆山、嘉定一帶的抗清武裝斗爭。起義失敗后,他開始了漫長的逃亡生涯,隨行的騾馬馱著書籍,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清順治十三年(1656),只身北上,十謁明陵,遍游華北,所至訪問風俗,搜集材料,尤致力邊防和西北地理研究,并墾荒種地,結納同道,以圖恢復。康熙七年(1668),為山東“黃培詩案”株連入獄,經友人營救獲釋。
顧炎武律己極嚴,身處逆境而終無頹唐之想,剛正不阿,堅毅不屈,一生誓不與清廷為伍。其詩《精衛》寫道:“嘗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對于投清變節者,他毫不留情,憤然直斥:“薊門多狐鼠,舊日須眉化兒女”。康熙十六年(1677)開博學鴻詞科,都中爭相舉薦,他致書曰:“刀繩俱在,毋速我死。”并鄭重聲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次年議修明史,總裁葉方藹又特邀他入明史館,他嚴詞拒絕,回信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卷三)其超行氣節,令清廷都敬畏不已。
此后,顧炎武客居山西、陜西,潛心著述,不再入世。晚年筑土室于華陰叢冢間,與妻偕隱,自署門聯云:“妻太聰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并說:“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可見即使隱居,仍不忘其志。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曲沃。
顧炎武閱歷深廣,學問淵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見者已有 50 余種,代表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韻補正》、《亭林詩文集》等。他于經史百家、音韻訓詁、金石考古、方志輿地,乃至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水利河漕、兵農田賦、經濟貿易等都有精湛研究,為清代學術開辟了眾多門徑。如在經學上,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注重確實憑據,辨別源流,審核名實,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范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在音韻學上,考訂古音,離析《唐韻》,分古韻為十部,在闡明音學源流和分析古韻部目上,有承前啟后之功,被譽為古音學的奠基者,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學五書》中。
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為其鮮明旨趣,認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并以其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清代樸學的先路,對吳、皖考據派有深刻影響,被譽為明清學問有根柢第一人,成為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思想家。
顧炎武強調為學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秉承“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古訓,認為對社會歷史(“文”)的探討和操守氣節(“恥”)的砥勵,同樣重要;還提倡“利國富民”,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他大膽懷疑君權,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更是影響深遠,流傳至今。
顧炎武的治學思想同樣貫策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主張作品應為“經術政理”服務,認為“文須有益于天下”(《日知錄》),“故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人書》三)。又說:“詩不必人人皆作”,“和韻最害人詩”,反對一切阿諛、剿襲及無聊的應酬文學,提倡嚴肅的創作態度。他主張“詩主性情,不貴奇巧”,但并不一般地反對運用技巧。他指出《漢書》“束于成格,而不得變化”,《史記》則“情態橫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認為《漢書》不如《史記》。他反對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評一位朋友的詩文說:“君詩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韓、歐。有此蹊徑于胸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與人書》十七)
顧炎武的文學成就主要以詩見稱,現存各體詩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顧詩箋注》的《集外詩補》中所收的4首佚詩。顧炎武生當亂世,詩歌創作的現實性和政治性十分強烈,形成了沉郁蒼涼、剛健古樸的藝術風格和史詩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沈德符評他:“肆力于學,……無不窮極根柢,韻語其余事也。然詞必己出,事必精當,風霜之氣,松柏之質,兩者兼有。就詩品論,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詩別裁》)如著名的七言律詩《海上》四首,關心恢復事業,悲感蒼涼,林昌彝在《射鷹樓詩話》中便評曰:“獨超千古,直接老杜。”
清軍南渡,一路燒殺淫掠。顧炎武寫下了一系列國亡家破、長歌當哭的壯烈詩篇。他在《秋山》中描寫江陰、昆山、嘉定等地人民抗清失敗后被屠殺劫掠的慘狀:“旌旗埋地中,梯沖舞城端。一朝長平敗。伏尸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烈火吹山岡,磷火來城市。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荊杞”。楊廷樞、陳子龍、何騰蛟等抗清不屈而死,他都作詩哀悼。他起初寄希望于南明政權,在《京口即事》中,他將督師揚州的史可法比作東晉志圖恢復的祖逖。南明唐王遙授他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他收到唐王的詔命后十分激動和興奮,《延平使至》詩中寫道:“身留絕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戟班”。南明政權相繼覆滅,使他深感悲痛,以“春謁長陵秋孝陵”(《重謁孝陵》)寄托胸懷。《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雁》、《元旦》、《又酬傅處士次韻》、《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井中〈心史〉歌》等,都表現了他直至垂暮之年,懷念故國之心仍耿耿不釋。
顧炎武同時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書信筆鋒銳利,議論文簡明宏偉,記事文如《吳同初行狀》、《書吳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軍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風亮節,讀來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躍然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