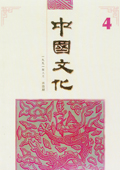
《中國文化》第4期(1991年8月)
主 編:劉夢溪
主 辦: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編輯部
周 期:半年刊
出版時間:1991年8月
編 後
本刊編輯部不久前舉行了一次《中國文化》創刊周年學術座談會,在京的學術顧問和對本刊的創辦始終給以熱切關注的資深學者二十餘人蒞會。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先生、香港中華書局助理總編鍾潔雄女士,分別介紹了《中國文化》在大陸和香港、臺灣出版發行情況。沒想到這樣一本專業性很強的純學術刊物,還擁有那麼多讀者。大陸版第一期印2000冊,很快銷售一空,於是第二期起改印3000冊。
季羨林教授在發言中說:“《中國文化》的出版,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有人斷言這個時候它不該出,本意是說它出不來。現在出來了,還能夠脫銷,不能不讓人驚奇。看來不能低估中國讀者的眼光。”吳組緗先生說:“文化和歷史是伴生物。沒有文化的歷史和沒有歷史的文化都難以想像。不瞭解歷史,講愛國主義就缺乏依據,講唯物論也靠不住。”舒蕪先生說:“電視裏播歷史劇,總以為可以獲得一些歷史知識,但常常掃興關機。比如有個劇本,演到魯迅要辭職,別人挽留,一口一個‘樹人兄’,應當是‘豫才兄’嘛。又如總督稱自己‘卑職’,這都是鬧笑話。”因此他們贊成重視歷史文化研究的辦刊方針。周汝昌先生談到,中國的藝術與文化有自己的特徵,但不同意一個時期流行的那種抽象比較,如說“西方文化是動態的、外向的、向前的,中國文化是靜止的、內向的、反省的”等等。他說:“魯迅是一代文豪,可他對中醫有偏見。偏見不影響魯迅的偉大,也不影響中醫的發展。中醫和西醫是兩個勁兒。西醫講解剖學,中醫重視人體的表裹寒熱虛實,認為生機一旦停止,就難以掌握生命體的周流運行的各種關係,這是兩種看待宇宙萬物人生世界的態度。”趙樸初、周有光兩位先生提出,應從世界的角度來觀察中國,這樣才能參與人類文化發展中的整體對話。李學勤先生說:“中國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很有意思,明清時期不會有中國文化之說。只有從世界文化的大背景出發,才好談中國文化。”馮至先生年來很少參加會議,但看了《中國文化》,覺得有話要說。第一期刊載的王伯祥先生的遺稿中,有“不茍不欺自勉”的話,他說這是中國文化所要求的一種境界,弄文字的人應該共勉。任繼愈先生和龐樸先生建議,研究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文化的文章應給予重視。馮其庸先生主張立足於自己,認為承繼了傳統,文化的建設才有根基。嚴紹璗先生希望注重傳統文化的現代詮釋。樂黛雲先生說:“人文學科的後繼人才問題令人擔憂。北大歷史系89年設有招生,90年中文系錄取的不少是第二志願。文史哲終究是文化的核心,不重視人才培養,容易形成學術空檔。”作家王蒙說:“就學術的力量而言,冷文化比熱文化力量大。”李澤厚先生插話:“《中國文化》創刊之初我就提議,不妨搞一點冷文化。”
參加此次座談會的多是精聞博洽的宿學碩儒,出於對中國學術與中國文化的眷愛和前瞻性思考,對本刊寄望甚殷。我們還接到張光直、周策縱、傅偉勛、汪榮祖、李又寧、高辛勇、王潤華等海外學者的信函,也對《中國文化》勖勉有加,並提出一些使刊物辦得更好的建議。在德國基爾大學學習日爾曼語言文學的一位叫朱爾寧的留學生,寫信來要求訂閱《中國文化》,信中寫道:“幾年前,當人們開始對中國文化發難的時候,我們在校園裏也跟著激動憤然了一番。後來跑到歐洲來,看到這裹的人們由於中國文化的神秘性而產生崇拜——一種盲然的崇拜。人人都會順口滑出中國文化四個字,但誰也解釋不清那是什麼。”他說也許讀了《中國文化》雜誌“可以撕開那無垠天幕的一角。”莘莘學子之心,其情可憫,但讀到刊物之後。他也許會失望罷。
因為說到底《中國文化》只不過是一本刊物而已,編者的眼光和識見難免不存局限。何況操持此刊,常感困難重重。自籌資金就頗為耗時費力。但學界同道師友的厚愛和讀者的期待,使我們在選題組稿時不敢稍忽,總希望每期都能集中解決或至少探究幾個有關中國文化的學術難題。這期“文史新篇”專欄裡的三篇文章,便是此種努力的一部分。古代數術家用以占驗的工具“式”,歷年出土所得共有八件,大都是漢代原物,包括天盤和地盤,分漆木式、象牙式、銅式等不同種類,其構造、功能應用頗具神秘色彩。國內外發表的研究古式的論文有l5篇,但言人人殊,難定一尊。李零的《“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一文,可以說對這一問題提出了系統的帶總結性的圓解,文字雖長,卻能夠引發讀者的興趣。而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是他辭世前撰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舊而彌新的大課題,其中一段寫道:“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以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整篇文章未來得及展開,但思路明晰,結論確定,包孕著作者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終生體悟。恰好本刊自創辦以來就很注意這方面的問題,所以第一期發表《火曆鈎沈》,選取的就是從天文學探考中國古代文化發生的角度。第三期又刊載通譯互釋北極、太一、道、太極的文章,並在編後記中申論自然崇拜和神的崇拜的關係,認為《老子》二十五章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中國文化的認知循環圈。本期“文史新篇”專欄的文章,對此一課題的探討又進了一步。
就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而言,1990年是文星殞落的一年。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這一年過世。此前不久,老作家臺靜農病逝於臺北。大陸則有老作家俞平伯、詞學家唐圭璋、古史專家徐中舒、哲學史家馮友蘭等相繼病故。1990年同時也是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誕生一百周年。1991年是胡適先生誕生一百周年。對此本刊特在“現代文化現象”專欄列出四篇文章。以表示我們的追思與紀念。馮友蘭先生晚年自署的一幅聯語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這種境界也是我們《中國文化》所追求的——“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編後記
文章分頁: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