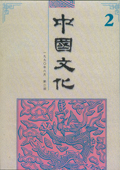
《中國文化》第2期(1990年6月)
主 辦: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編輯部
周 期:半年刊
出版時間:1990年6月
編 後
讀者從目錄中可以看出,這一期的敦煌學研究和中國藝術研究是兩個重點課題。敦煌學的學科很多.季羨林教授主持的筆談,分別從語言文學、宗教學、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研究、唐代均田制研究和敦煌目錄學五個方面,報告了這門專學近年所獲得的成果。姜亮夫先生的文章,係根據在1988年國際敦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相當於一篇縮寫的敦煌學述。白化文、李鼎霞兩先生校錄的敦煌《諸文要集》殘卷,亦頓有文獻價值。相信此組文字會引起敦煌學者和熱心敦煌學的讀者的興趣。
中國藝術是個絕大的題目,領域十分寬廣,本期刊載的七篇論文,只是從書法、美術、戲劇等某一個側面來探討中國藝術的美學特徵和文化意蘊,但作者都是名家,不乏深湛之思與會心之得。周汝昌先生以“??學”名中國書道,為最能體現中國藝術精神的書法一種重新樹名立義,文章值得一讀。吳甲豐先生對謝赫“六法”之一的“傳栘模寫”衍變過程所作的考察,可以在理論和創作實踐兩方面啟發美術愛好者的思路。常任俠先生和馮先銘先生的文章。則涉及到中外藝術相互影響和文化交流問題,說明吸收異質文化是刺激本民族藝術發展的重要因素。
“文史新篇”專欄披載的《寒食與改火》一文,是裘錫圭先生的精心之作,從民俗學和比較文化學的角度考論相傳已久的介子推焚死的故事,得出了富有說服力的結論。饒宗頤先生在探討遠古時期的日月崇拜時,對大汶口陶文的解釋不同於龐樸先生在《火曆鈎沉》中提出的觀點,這種學術上的切磋之風誠如陳寅恪先生當年所說,頗類似佛教的所謂因緣,本刊願倡導之。其它專欄裏的文章,如趙岡論中國古代的私有產權與市場經濟、黃子平運用敘述學的理論和方法解析魯迅的《故事新編》、趙昌平闡釋盛唐詩歌的形成與分期、陳平原追尋武俠小說如何最終走向文人化,選題立論均相當精慎,非一般泛泛之作。小說家汪曾祺的兩篇《城南客話》也很好讀。此外。王邦維整理的《陳寅恪讀高僧傳批語輯錄》,以及沈從文的遺稿《說熊經》(附圖)、王?的《八角星紋與史前織機》,更是學界不可多得的“絕活”,值得向讀者鄭重推薦。
編完這一期,已接近農曆庚午年新春,我們心裏充滿了對學術界師友同道的感謝之情;沒想到本刊確立的潛心學術、探究真知、重視專學、弘揚文化的宗旨,得到如許廣泛的支持和共鳴,友聲道聲不絕於耳。使我們對進一步辦好《中國文化》有了更多的信心。
一九九O年一月十五日編後記
文章分頁: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