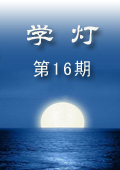
《學燈》2010年第4期(總第16期)
主 編:李銳 朱清華
周 期:季刊
出版時間:2010年12月
嚴復1913年9月“民可使由之”演講新詮
李海默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認為,1913年9月3日嚴復的《民可使由之》演講,其“道德”部分是說給梁士詒聽的,“宗教”部分是說給陳煥章聽的,“法律”部分則是說給有賀長雄聽的,三個部分環環相扣,意旨交織,表達了嚴復既排斥孔教會中人的“教主”傾向,也排斥袁世凱僚屬們以自身知識立場“誤導”袁世凱的傾向的思想意旨。嚴復對于孔教一事基本立場可能在于,以神道之“幽”,神道之“由誠而明”,遏制其使“人理”受制于“神道”的傾向,為“民義”造“根蒂”,使人道之教得以“由明而誠”,而不至于“執民業而忘天道”(針對袁世凱僚屬“誤導”之謂),或“以一曙之智慮”,以一二人而“劫制號令”,不審“其事之所由來”,徑謂“可取而代之”(針對孔教會徑奉“教主”傾向之謂)。
1913年9月3日,孔教會在北京國子監舉行祭孔儀式,由眾議院議長湯化龍主祭。袁世凱特派梁士詒為代表前往獻香。會上講經者為梁啟超、嚴復兩位名儒,梁講《君子之德風》、嚴講《民可使由之》[1]。
關于嚴復與孔教會之關系,既有的研究已比較豐富。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曾指出,嚴復和梁啟超在日益分崩離析的環境中越來越堅信,中國需要能夠穩定共同的信念的起碼的基本要素,嚴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于1913年8月在孔教會的請愿書上簽了字,要求定孔教為國教[2]。史華慈此論為后來學者探討開創了基礎,此后的進一步討論,在大陸地區,可以皮后鋒、張頌之與韓華三人為代表,在臺灣以及海外,可以黃克武為代表。
皮后鋒在其著作《嚴復大傳》中指出:嚴復積極參加尊孔復古運動,在動機上是出于對鄙棄傳統文化可能導致立國精神喪失的深深憂慮,其所作所為是為了彌補荒經蔑古的偏頗,根本沒有為復辟帝制服務的意圖[3]。張頌之認為,1912年辛亥革命之巨變,使嚴復這位曾勸說梁啟超“教不可保,亦不必保”的思想家,轉而支持康有為的孔教主張,但另一方面,嚴復此時的贊同尊孔,與孔教會諸人可能還有不同[4](值得注意的是,張先生的意見是將《民可使由之》演講看作嚴復轉而支持康有為的依據之一)。韓華認為,梁啟超、嚴復等人,視孔教為中國的國性,但并不完全認同國教。在這些人看來,國性是維系中國的命脈,保孔教即保國性,振興以孔教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是挽救人心渙散的良策,是規范社會秩序、政治秩序的必由之道[5](韓華還曾指出,當時孔教會可以通過嚴復及進步黨議員在國會內倡言孔教,呼吁通過國教案[6])。皮、張、韓三位先生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也是比較平正的。
臺灣學者黃克武的見解則更為細膩,他發現,嚴復1913年的《民可使由之》演講反映嚴復抱持著精英主義(elitism)的立場,對他來說知識分子與一般老百姓,在智慧方面幾乎有一道永恒的裂痕,人們不能期望一般老百姓對道德、宗教、法律有深入的了解之后,再遵循這些規范。這種跡象顯著地說明,嚴復在思想上更為強調傳統文化的價值[7]。
綜合諸家觀點,不難發現,《民可使由之》演講本身蘊含著豐富、多維的意涵,而且傳達的是極其關鍵的一種象征著嚴復思想變化趨勢的意旨。筆者認為,必需由此次演講之前后時序來進一步摸索,方能得其更深一層之真義。
一
首先必需明確的是,1913年9月的北京國子監祭孔儀式是一次怎樣性質的活動。
據當時的《孔教會雜志》載:“是日到會者千余人,有外國報界、教界、外交界人員參觀。大總統袁世凱代表梁士詒,眾議院議長湯化龍,廣東省民政長陳昭常參加獻禮。梁士詒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并稱:‘大總統有種種困難,深望社會上有賢人君子出,而道民以德,且深望國會中人,早宣各種法律,俾收齊民以禮之效’”,在《孔教會雜志》的報道中,梁士詒與梁啟超的演講都被作了若干摘錄,而嚴復的演講內容卻只字未提,僅載其題目[8]。倒是《憲法新聞》的相關報道上載:“三者皆能闡發圣教,聞者感嘆不置”[9]。另據《憲法新聞》的報道,此次集會由梁士詒任主祭者(另一說為湯化龍),程序是行完跪拜禮后,由陳煥章任主席,主持講經。而據孫應祥先生《嚴復年譜》,尚有王錫蕃與日本顧問有賀長雄與祭[10]。據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一書中所搜集相關史料,尚有龍澤厚與李時品[11]二人。也就是說,在拜祭的程序里,由梁士詒代表袁世凱主持,之后的講經程序里,陳煥章任主席,他先行闡述了舉行丁祭的宗教意義與現實意義[12],然后依次由梁士詒、嚴復、梁啟超講演(此順序《孔教會雜志》與《憲法新聞》皆同)。這樣,整個祭孔活動的十名關鍵人物便也弄清楚了,分別是梁士詒、湯化龍、陳昭常、陳煥章、嚴復、梁啟超、王錫蕃、有賀長雄,龍澤厚,李時品(其中4人為粵人,另加嚴復一位閩人,湯化龍一位鄂人,王錫蕃[13]一位魯人,龍澤厚一位桂人,李時品一位川人),王錫蕃、李時品、龍澤厚、陳煥章當時都是孔教會骨干[14],梁士詒、湯化龍、陳昭常[15]、有賀長雄是袁世凱政府要員,在此格局下,嚴復與梁啟超的確有不歸屬于這兩個集團中任何一個的相近似之處,韓華指“梁啟超、嚴復等人,他們視孔教為中國的國性,但并不完全認同國教”是其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于嚴、梁二人仍以學者本位自居,既非宗教策動家,也非政治策動家。1913年9月孔教會國子監集會請這二人演講,一方面當然是基于他們的學術大名,但另一方面則未嘗不是希望能在宗教家與政治家之間做出由學問家來調和的姿態。
此外,事件的另一個關鍵之點是,拜祭程序里曾行跪拜之禮。
為什么要特別強調跪拜之禮呢?在孔教會“仲秋丁祭祀孔”一事后不久,9月28日,孔子誕辰,教育部總長汪大夑令全體部員前往國子監祭孔,魯迅在其日記中記載:“昨汪總長令部員往國子監,且須跪拜,眾已嘩然。晨七時往視之,則至者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錢念劬(錢恂)又從旁大聲而罵,頃刻間草率了事,真一笑話。聞此舉由夏穗卿主動,陰鷙可畏也”。我們須知,9月23日,有趙炳麟議員提議立孔教為國教事,故28日汪大夑令教育部部員前往祭孔,此時形勢已較9月初孔教會祭孔時更為熾烈,而教育部又為袁世凱政府中樞直屬機構,其部員尚且如此抗拒行跪拜禮,可見9月初孔教會行跪拜祭孔之禮,雖于其自身而言不算什么驚天之事,于外界卻必然是遭致物議極多的。再看梁士詒所致詞,其基本理路全然來自6月22日袁世凱的《尊孔崇圣令》,其令文有云:“值此诐邪充塞,禮法蕩然,以不服從為平等,以無忌憚為自由,民德如斯,國何以立”。因此,如果相信此次祭孔活動中尚有出于袁世凱意志之外的變數,則端視梁、嚴二人之講演。
嚴復既在梁啟超之前演講,則其選“民可使由之”為題,是很值得玩味的。康有為在1902年完成的《論語注》中稱:“孔子之欲明民至矣。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如以神道設教,則民以畏服,若明言鬼神無靈,大破迷信,則民無所忌憚,惟有縱欲作惡而已。故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無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凡此皆至易明者。孔子深憂長嘆,欲人人明道。若不使民知,何須憂道不明而痛嘆之乎?愚民之術,乃老子之法,孔學所深惡者。圣人遍開萬法,不能執一語以疑之。且《論語》六經多古文竄亂,今文家無引之,或為劉歆傾孔子偽竄之言,當削附偽古文中”[16]。此處“神道設教”之謂,后成為康門一個重要的學術指標,10年后的1912年底,陳煥章出版《孔教論》,即認為:宗教有“人道之教”和“神道之教”的差別,前者主要著眼于人倫,而后者則主要著眼于對于神靈的信仰,“孔教兼明人道與神道,是孔教之為宗教,毫無疑義,特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實可行,乃偏重人道耳”,陳煥章還指,英文的religion,基本上偏重于“神道”,因此與中文中的“禮”的意思接近,既然中國人早有“禮教”這種稱呼,因此將儒家說成“孔教”是天經地義的[17]。康門中人甚至有人持見,實際上孔教的“人道之教”是從“神道之教”進步而來,屬于一種更高級的宗教[18]。綜合起來看,從康有為開始詮釋此語到孔教會大行其道,10余年間,對此語的理解已基本定型:首先,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實可行”,故其“欲人人明道”,不需懷疑;其次,孔教本有“禮教”,亦即“神道”之一面,故意在“民以畏服”,路徑之一便是“使民重祭祀,而鬼神之有無生死,不必使人人知之”,第三,孔教的“人道之教”是從“神道之教”進步而來,不可完全脫去后者面貌,否則“民無所忌憚,惟有縱欲作惡而已”。由此觀之,此語對于孔教會組織系統而言已是有鐵板釘釘之結論,而其人請嚴復演講,最初當不意嚴復竟會選擇此已鐵板釘釘之語而再做闡發。
1903年,嚴復譯《群學肄言》在上海出版,其第十二篇《教辟》中即言:“近世愛智之家,有為人道新教以代神道舊教者,其說為虛愿,而不可實見于施行也。夫人道之教出于思,由明而誠者也,神道之教本乎信,由誠而明者也,顧欲祖仁本義,由一切人事之宜而張為法制,此在上智猶或難之,況彼中材之眾庶。且彼所訾于宗教者,惡其既古而所本者虛也,則不悟一宗教之行能歷數千年而無墮者,其所昭示創垂而以為坊民之紀者,豈皆虛哉夫,亦以人事之得失征之耳。故宗教所垂之懿訓嘉言而為人事之經法者,固非竭一人之思索辨問而為之也,乃積數百千年人事之閱歷甘苦而得之。當此數百千年中人類之所為,固不知幾經拂亂,茫乎其是而從其非,從其非則禍患痛苦死亡從之,而非之途乃以漸廢,是之途乃以獨存,而以為后世法。是故宗教雖人事之經,而亦天演之事,經物競天擇之淘汰,而有此余也。然則宗教者,固人事之科律,而其所以垂為后法者,非一二人之劫制號令也,閱數百世之治亂興衰,積累試驗合而成此,故其說多堅,而其理多信,而后之人,欲以一曙之智慮,謂可取而代之,夫亦于其事之所由來未深審歟?”,又云:“不寧惟是。夫以人道之教代神道之教者,就令竭其心思而所以綱紀人倫者釐然悉備,是教也,其果可施行而效矣乎?是尚不可得而知也。何以言之?人特謂人心之所信守與其行事之所率循者,皆出于知,而不悟其非也,知僅為其得半之途耳。蓋凡人之行誼,其定于情而不由夫理者,蓋什八九也”[19]。在這段話中,嚴復核心意旨在于闡明“宗教雖人事之經,而亦天演之事,經物競天擇之淘汰,而有此余也”,“其說多堅,而其理多信”,對于這個“凡人之行誼,其定于情而不由夫理者,蓋什八九”的客觀存在的世界,“就令竭其心思而所以綱紀人倫者釐然悉備”,也是不足應對裕如的。嚴復清楚地認識到,宗教使“人理”受制于“神道”,即以神道設教的戒律教條為至上,而不是以鮮活的“人理”“民生之幸福”為旨歸的弊端,他的化解策略在于“宗教之精義存于幽,幽故稱神道,而后之人欲以民義之顯者易之,此不僅求之心理而不然也,即考之往跡莫有此者。夫人道之尊固也,然嘗有物居民義之先,而為根蒂者矣。執民業而忘天道者,可以為一時,不可以為永久。”故有所謂“人道之教出于思,由明而誠者也,神道之教本乎信,由誠而明者也”。即以神道之“幽”,神道之“由誠而明”,遏制其使“人理”受制于“神道”的傾向,為“民義”造“根蒂”,使人道之教得以“由明而誠”,而不至于“執民業而忘天道”,或“以一曙之智慮”,以一二人而“劫制號令”,不審“其事之所由來”,徑謂“可取而代之”。嚴復1903年此種見解,與一年前康有為之論已是有所區隔,與近十年后孔教會大行其道時的論點更是深有不同。
二
明乎此點,可以進一步討論嚴復的“民可使由之”講義[20]。
嚴復先說:“孔子此言,實無可議,不但圣意非主愚民,即與‘誨人不倦’一言,亦屬各有攸當,不可偏行。淺人之所以橫生疑謗者,其受病一在未將章中字義講清,一在將圣人語氣讀錯”。嚴復說,“民”字乃統一切氓庶無所知者之稱,“而圣言之貫徹古今者,因國種教化,無論何等文明,其中冥昧無所知與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數。茍通此義,則將見圣言自屬無疵”,又指章中“不可”二字乃術窮之詞,“淺人不悟,乃將‘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語,全作禁止口氣,爾乃橫生謗議,而圣人不得已詔諭后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至此,嚴復所云與康有為并無顯著不同,而以下部分,嚴復將就“之”字詮釋其獨到之立場。
嚴復指,“之”字所代者主要系三物,“道德一也,宗教二也,法律三也”。先言道德,嚴復指,“道德為物,常主于所當然,而不若學門之常主于所以然。夫所以然,乃知之事;而所當然,乃由之事。使必先知而后有由,則社會之散而不群久矣!然則所謂可使由,不可使知,民之于道德也已如此”。從表面上看,嚴復只是說民之于道德應“可使由,不可使知”,然而筆者認為,此處實與梁士詒致詞相關聯,梁士詒所謂“大總統有種種困難,深望社會上有賢人君子出,而道民以德”,側重正在于“知”,嚴復深意,實在表明對梁士詒之不能茍同,往更深一層說,有理由相信嚴復的主張是,如果按照梁士詒的理路,由賢人君子助大總統使“民”知德,則詮釋的尺度與口徑將全系之于官方,民如不知德,尚且可以依循“由”德之路徑而制衡官方,而如民被道之以德,則勢將完全失去獨立性,而進一步“定于情而不由夫理”,導致“社會之散而不群”,社會既“散”,則無以制衡官方。嚴復當時持“舍己為群”之見,故要力抗“社會之散而不群”。1902年2月,嚴復致書吳汝綸女婿王子翔,請他“以舍己為群之義”勸吳氏救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之職務。3月,嚴復轉變態度,同意應聘為譯書局總辦,論者或謂也可能是出于“以舍己為群之義”[21]。
嚴復次言宗教,云:“社會之有宗教,即緣世間有物,必非智慮所得通,故夫天演日進無疆,生人智慮所通,其范圍誠以日廣,即以日廣之故,而悟所不可知者之彌多。西哲嘗云:‘宗教起點,即在科學盡處’。世間一切宗教,無分垢凈,其權威皆從信起,不由知入;設從知入,即無宗教”。如聯系前揭嚴復《群學肄言》文段,“人道之教出于思,由明而誠者也,神道之教本乎信,由誠而明者也”,可知嚴復此處在講其“神道之教”,嚴復對此理解本與陳煥章以至孔教會諸人有所隔閡,嚴復深懼使“人理”受制于“神道”,故欲以神道之“幽”,神道之“由誠而明”遏制乃至化解,孔教會中人則相對更強調祭祀之功效,認為“神道之教”主要著眼于對于神靈的信仰,神道之“幽”,神道之“由誠而明”在其語境中是相當無足輕重的。
在嚴復之前陳煥章所作的演講里,他指出:“《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齊其政者,即明定國教之謂;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者,即信教自由之謂……《中庸》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者,國教之所以獨尊也;小德川流者,信教之所以自由也。并行不悖,此孔教之所以為大也”,是故“中國自古皆奉孔教為國教,亦自古許人信教自由”。陳煥章在此強調“宗教之禮,尤以守舊為貴焉,其教之形式在是,其教之精神亦即在是”,而祭祀儀式則是宗教的一大要素,決非細故,它與“教之存亡,固大有關系”[22],陳煥章指:“當創造政令之后,不可不有教以丁寧告誡之,當申明政令之前,亦不可不有教以叮濘告誡之,宗教實為政治之中樞,無宗教以先后之,則政治必不能行,故政教者,相依為命者也,中國不能無教,故中國不能無丁祭”。陳煥章由祭祀而談及“政教者,相依為命者也”,其“當創造政令之后,不可不有教以丁寧告誡之,當申明政令之前,亦不可不有教以叮濘告誡之”顯示了與嚴復所持“悟所不可知者之彌多”見解迥異的傾向,若再聯系嚴復未說出的內在語境,則可以知嚴復亦有與陳煥章對峙的意旨在。
再次言法律,也是嚴復耗費筆墨最多之處。嚴復指:“夫法律者,治群之具,人之所為,而非天之所制也。然則其用于民,似可使由而兼可使知,莫法律若矣!……(但是)無論何等社會,民之程度莫有至者……即在文化大開之國,其中法令,本于隨時之義所不得已,而有事者常若牛毛……至于法令繁興之后,欲明法典之統系與其解釋請比之宜,每資專門畢生之學而后能之,使必知之而后有由,將法律之行無日。且諦而言之,此能由而不盡知者,其于民德治柄亦非無所利也。西國法家謂法律之行于民,猶夫道德之條誡,轉不欲劃然分明,制為畛畔,使持循者嚴于文字而棄其精神。……身為國民,皆有服從法律之義務,顧從其大者言,法之所求至易盡也……凡斯種種,幾于盡人所知,設其犯之,固亦自知有罪,至有嫌疑難明之獄,俟精辨而后,是非以明。則國家設置理官,訟者延雇辯護,正以為此。彼編戶齊民,固不必深諳科律,使得舞文相遁,或緣法作奸,以為利已損人之事。是故風俗敦龐之國,其民以離法甚遠之故,于法律每不分明,而錐刀堂爭之民,其國恒難治,其民德亦必不厚也。由斯而論,則雖在法律,其于民也,亦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何則,知之轉于亂而近于治遠耳。”嚴復在此將法律“使知之”可能產生的弊端歸納為:1,使必知之而后有由,將法律之行無日;2,可能“使持循者嚴于文字而棄其精神”;3,可能“使得舞文相遁,或緣法作奸,以為利已損人之事”,三者歸結起來將“知之轉于亂而近于治遠耳”。
從表面上看,嚴復在此針對的就是一般意義理解的法律,然而筆者認為嚴復實際的靶子是臺下的有賀長雄。
1913年8月,作為袁世凱法律顧問的有賀長雄發表《憲法須規定明文以孔教為國家風教大本》,文中以德、英等國的憲法為證,指“國家既于憲法保證信教自由,而復公認一宗以為國教,而特別保證之,利用之,此與立憲政體,未嘗相決。”且孔教“尊祖祀天,不言神秘甚密之義。而于人倫則至纖至悉,鄭重周詳,是故倫理者乃中國文明之精華,為西漢以來二千年間政教之基礎,其浸潤于國民意識至深,其支配國民精神之力極大。居今而言保守,不但須將通國之中所有被服儒術,崇奉孔教者總為一團體,由國家公認而保護之,且于憲法特著明文,以此為國家風教大本。”[23]嚴復所指法律應“使由之”的三點理由實質應在于反對有賀長雄“憲法須規定明文以孔教為國家風教大本”,如有賀長雄意見得到施行,嚴復期待能夠發揮效力的神道之“幽”,神道之“由誠而明”將永無出頭日。嚴復表面反對的是將法律“使知之”,而更深層次的意涵在于反對政教相混同,教借政而上位,政借教而自肥,在于紹述中國學術體系中固有的“天人相分”之傳統[24]。
故筆者認為,嚴復演講“道德”部分是說給梁士詒聽的,“宗教”部分是說給陳煥章聽的,“法律”部分則是說給有賀長雄聽的,三個部分環環相扣,意旨交織。“法律”部分耗費筆墨最多,原因當正在于有賀長雄學術位置最重要,且系外人中的學術巨子,斯賓塞學說最初入華即由華人翻譯有賀長雄《人群進化論》、《社會進化論》等著作開始[25]。嚴復費心闡釋其與有賀長雄的區異之處,更于演講結尾處說自己“非效時賢數典常忘,侮圣言而夸丑博”,此演講本身包涵之戰斗性當非筆者信口虛言。
三
梁啟超接著嚴復的演講《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今似已不能見到原本[26]。就《孔教會雜志》所錄來看,似比較折中,有打圓場之態,但正如沙培德讀出的那樣,梁氏案下似乎說明,即使君子只占相對的少數,亦足以將整個道德衰敗的趨向幡然丕變的[27],筆者認為,梁啟超此處的少數“君子”,與其說是針對孔教會與袁政府班底之人而發,不如說是針對嚴復而發。正如黃克武先生曾指出的,雖然嚴復與梁啟超顯然都不夠了解西方市民社會中的“公民精神”,更談不上以此為基礎來相互合作,雖然嚴復一方面不夠自覺到自身前后論述的差異,另一方面又不理會1903年之后梁啟超轉向調適[28]的思想變遷,不斷批評梁啟超,但梁啟超基本上都是在默默地接受嚴復這位前輩的批評[29]。或許正是梁啟超這種態度,導致后來袁世凱欲以四萬金請嚴復撰文反駁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時,為嚴復所卻之。
嚴復有一個始終都堅信的“今之道與今之俗”的論式,這個論式認為,如果我們只是盯著西方的“技藝”,想讓它在本土開花結果,而不改變“本土”之“俗”,即它生長所需要的合適“土壤”,結果只會是“淮橘北枳”,難得其效,關鍵是把“西體”也要放在“新學”之中,并把它移植到“本土”中來,使“新學”之“體”與“新學”之用相得益彰[30]。
王憲明先生曾將嚴復的《民國初建》詩中的“美人”解作袁世凱的復出而非指中華民國的成立,進而認為全詩的真正精神并非渴望中華民國早日成立,而是暗示希望袁世凱早日出山,以代替清政府與南方新政權來收拾辛亥革命以后出現的混亂局面[31]。如果此點確乎可信,則嚴氏“民可使由之”演講的意旨似乎在于既排斥孔教會中人的“教主”傾向,也排斥袁世凱僚屬們以自身知識立場“誤導”袁世凱的傾向,他似乎意在將自身對孔教問題異于時流(在其語境中,神道之“幽”,神道之“由誠而明”,乃是“西體”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的看法表達出[32],并期待能為袁世凱所用之。韓華曾指出的袁世凱提倡尊孔,卻不主張立“教”,尤其不主張尊孔教為“國教”,未嘗不可以說是一定程度上受到嚴復影響。
誠然,嚴復的見解也極形晦澀,且易流于空想,但其立場如確有精微細致,回旋轉折之處,則其內在理路(inner logic)的延展,是我們所不應當忽視者。
附錄:嚴復的“慧眼獨識”
筆者在近期完成的一篇論文中通過文本分析,認為1913年9月3日嚴復的《民可使由之》演講,其“道德”部分是說給梁士詒聽的,“宗教”部分是說給陳煥章聽的,“法律”部分則是說給有賀長雄聽的,三個部分環環相扣,意旨交織,表達了嚴復既排斥孔教會中人的“教主”傾向,也排斥袁世凱僚屬們以自身知識立場“誤導”袁世凱的傾向的思想意旨。嚴復對于孔教一事基本立場可能在于,以神道之“幽”,神道之“由誠而明”,遏制其使“人理”受制于“神道”的傾向,為“民義”造“根蒂”,使人道之教得以“由明而誠”,而不至于“執民業而忘天道”(針對袁世凱僚屬“誤導”之謂),或“以一曙之智慮”,以一二人而“劫制號令”,不審“其事之所由來”,徑謂“可取而代之”(針對孔教會徑奉“教主”傾向之謂)。在這篇論文完成后,筆者仍有一個問題困擾難解:雖然可以確信嚴復此篇講義意旨絕不在“愚民”,但究竟何以解釋黃克武先生所指出的此篇演講反映嚴復抱持著精英主義(elitism)的立場,“對他來說知識分子與一般老百姓,在智慧方面幾乎有一道永恒的裂痕,人們不能期望一般老百姓對道德、宗教、法律有深入的了解之后,再遵循這些規范”?如果確乎如此,那么嚴復的為“民義”造“根蒂”論說未免有些飄渺,有些迷離。
筆者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德人邁內克(Fridrich Meinecke)所著《馬基雅維里主義》一書,于此問題,方恍然大悟。此書中提到這么一段:“現代國家從開始抬頭上升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包含了一種內在矛盾或毒素。一方面,宗教、道德和法律對它來說都必不可少,都是它生存的基礎;另一方面,它一開始就立意在國家自我保存所需的任何時候損害它們”。這個見解若聯系上嚴復的這個演講文本,一切幽暗,似皆洞悉。
1913年的中國,不正是處于“現代國家開始抬頭上升的那一刻”嗎?一方面,袁世凱“竊國”的傾向正在潛滋暗長,另一方面,欣欣向榮的發展也無日無之,比如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即在是年展開。現代國家包含的那種“內在矛盾或毒素”日益浮出水面,嚴復在此時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創造性地提出“之”字所代者主要系三物,“道德一也,宗教二也,法律三也”,不正是講求要通過“使由之”來保存現代國家生存的基礎:宗教、道德和法律,而通過“不可使知之”來限制初具形制的現代國家“一開始就立意在國家自我保存所需的任何時候損害”宗教、道德與法律的傾向。我們可以拿一個例子來驗證,嚴復在此將法律“使知之”可能產生的弊端歸納為:1,使必知之而后有由,將法律之行無日;2,可能“使持循者嚴于文字而棄其精神”;3,可能“使得舞文相遁,或緣法作奸,以為利已損人之事”,三者歸結起來將“知之轉于亂而近于治遠耳”。其實這三點都是希圖保存法律施行、精神和正義效力的不受損害,抗拒那種“國家自我保存”的強大壓力。
嚴復曾指章中“不可”二字乃術窮之詞,“淺人不悟,乃將‘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語,全作禁止口氣,爾乃橫生謗議,而圣人不得已詔諭后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正因為現代國家脆弱無比,所以要用“術窮之詞”,待到現代國家規制日全,而能萌生出新的內在動力來應對這種“內在矛盾或毒素”時,“不可”這個詞自然要做更進一步的歷史調適,嚴復苦心,了然于此。
明白了這一層,我愿做一個更大膽的假設,雖然嚴復沿襲康有為,以“民”字乃統一切氓庶無所知者之稱,“而圣言之貫徹古今者,因國種教化,無論何等文明,其中冥昧無所知與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數。茍通此義,則將見圣言自屬無疵”,但實際上嚴復此處的“民”暗示著已經邁入現代國家之初階的中國國民,可以說是拿一個很高的標準來衡量,而且在筆者看來,嚴復語境中,不僅老百姓,即使那些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由于不通此義,亦當屬于“民”之行列,前者是現代國家雛形里的“冥昧無所知”者,而后者則是“程度不及之分子”。
為“民義”造“根蒂”,正是要逐步緩進,破除“智慧方面那一道幾乎永恒的裂痕”。
何以近百年前的嚴復能有如此精微的論說與思想體系,他的“慧眼獨識”,實在是由深明中西學術發生路徑之堂奧而來。
注釋:
[1]此事基本背景,可參閱肖瀾:《“函夏考文苑”之議相關政治因素》,《歷史教學問題》,2009年第5期。
[2]【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楊品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史華慈所撰第8章《思想史方面的論題:“五四”及其后》,471頁。
[3]皮后鋒《嚴復大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429頁。
[4]張頌之:《民國諸文化保守派眼中的孔教運動》,《齊魯學刊》,2008年第5期。
[5]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謝放教授指導,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后以同名出版,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
[6]韓華:《陳煥章與民國初年的國教運動》,《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7]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38頁。
[8]《孔教會雜志》,第1卷第8號。
[9]《憲法新聞》第17期《中外要聞·丁祭盛典紀略》,轉引自吳雁南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1840-1949)》,第二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33頁。
[10]孫應祥:《嚴復年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425頁。
[11]李時品系北京孔教會總干事,在后來國教案被否定時,曾致書嚴復求助,希望嚴復在國會內倡言孔教。李氏此信原載《知類疆立齋日記》,收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特刊·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12]陳煥章:《丁祭日國學講經介紹辭》,《孔教會雜志》第1卷第8號。
[13]王氏曾于1898年8月上奏推薦林旭、嚴復及另外兩人,當時王氏正熱衷于籌措一個叫“孔道會”的組織,其“一切章程,多承教于南海康先生”。
[14]當時康有為尚未就任孔教會會長,但早在1913年6月,北京姚君碻在致上海孔教總會的信中就說:“公舉孔教巨子一人,為全國孔教會長,奉南海為之魁”,轉引自張頌之:《康有為孔教會會長任職考》,《孔子研究》,2007年第4期。
[15]陳氏思想應屬較為西化,其與張元濟交情甚好。
[16]學者多以康有為曾斷此句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而正如黎業明先生指出的那樣:“康有為在《康子內外篇·闔闢篇》、《論語注》的相關章節以及《孟子微·自序一》論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時,并無這樣的句讀及相應的釋讀”,可參閱黎業明:《論近現代學者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詮釋》,《學術研究》,2007年第4期。
[17]關于此段文獻脈絡的重新組織,采用干春松:《康有為、陳煥章與孔教會》,《蘭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還可參閱同氏所著《制度儒學》一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可參閱黃克武:《民國初年孔教問題之爭論(1912-1917)》,收入中華民國建國文獻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建國文獻:民初時期文獻·第二輯·史著二》,臺灣,國史館,2001年。
[19]嚴復:《群學肄言》,北京,商務印書館,1926年,259-26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234-235頁。
[20]該講義當時曾載于《平報》與《憲法新聞》。文本收于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另可參閱盧云昆編選:《社會劇變與規范重建——嚴復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303-306頁。
[21]皮后鋒《嚴復大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231頁。
[22]可參閱韓華:《陳煥章與民國初年的國教運動》,《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3]此文收入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50輯。轉引自韓華:《民初孔教會與國教運動》,謝放教授指導,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
[24]高瑞泉《嚴復:在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對史華慈嚴復研究的一個檢討》,《哲學研究》,2007年第1期。亦可參閱拙作:《試說“氣類自繇”》,《讀品》(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主辦),第82期,2009年7月16日。
[25]可參閱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171頁。
[26]夏曉虹所編《飲冰室文集:集外文》(中卷)即僅收梁氏1914年在孔教會演講的《知命盡性》一文,夏書系200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27]【澳】沙培德(Peter Zarrow):《中國保守主義思想根源中的立憲主義與儒家思想——外來政治模式與民族認同相關之研究》,收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1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另可參閱同氏《辛亥革命后梁啟超之共和思想:國家與社會的制衡》,《學術研究》,1996年第6期。
[28]可參閱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29]黃克武:《嚴復與梁啟超》,收于張廣敏主編:《嚴復與中國近代文化》,福州,海風出版社,2003年。
[30]可參閱王中江:《近代中國思維方式演變的趨勢》,成都,四川出版集團,2008年,325-326頁。
[31]王憲明:《“美人”期不來,詩人自多情——嚴復〈民國初建〉詩“美人”新解》,收于劉桂生等編:《嚴復思想新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
[32]嚴復是“孔教公會”的發起人,其章程以“闡揚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