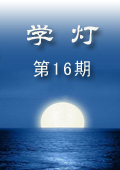
《學(xué)燈》2010年第4期(總第16期)
主 編:李銳 朱清華
周 期:季刊
出版時(shí)間:2010年12月
孔孟仁學(xué)比較:仁者愛(ài)人與惻隱之心仁也
萬(wàn)光軍
內(nèi)容摘要:仁是儒學(xué)的重要概念,在仁的界定上,孔子提出了“仁者愛(ài)人”,孟子提出了“惻隱之心仁也”,這涉及結(jié)構(gòu)與內(nèi)容,也涉及自然與社會(huì)。孔孟在仁上既有一致之處、又有區(qū)別所在。細(xì)致說(shuō)來(lái),孟子的界定表明他對(duì)孔子思想有所具體化、又有所狹隘化。在仁上,應(yīng)該由孟子向孔子回歸。
關(guān)鍵詞:孔子;孟子;仁者愛(ài)人;惻隱之心仁也
作者簡(jiǎn)介:萬(wàn)光軍:山東大學(xué)哲學(xué)與社會(huì)發(fā)展學(xué)院博士后,山東政法學(xué)院馬列部副教授。
仁是儒學(xué)的重要概念,關(guān)于仁,儒學(xué)歷史上主要有幾種說(shuō)法:孔子有“仁者愛(ài)人”、孟子有“惻隱之心仁也”、韓愈有“博愛(ài)之謂仁”、程朱有“仁者與天地萬(wàn)物為一體”等等。本文主要比較孔子的“仁者愛(ài)人”與孟子的“惻隱之心仁也”。孔子的話中包含著仁的主體及對(duì)象都是人,說(shuō)明了仁愛(ài)的道德情感是人才具有的、動(dòng)物暫時(shí)不包含在仁之中(傷人乎,不問(wèn)馬),這體現(xiàn)了人才具有道德的儒學(xué)基本立場(chǎng)。如暫時(shí)省略主體及對(duì)象,孔子的話似乎可以簡(jiǎn)略為“仁即愛(ài)”、或“仁,愛(ài)也”。孟子的話則是“惻隱之心,仁也”;如果把簡(jiǎn)化后孔子的話與孟子的話進(jìn)行比較,可以較為直觀地看到二者有聯(lián)系、有區(qū)別。就仁的不同方面來(lái)說(shuō),孔子的話可以說(shuō)是“仁者何為?”或“仁何為?”即仁的表現(xiàn)(作用)應(yīng)是愛(ài)人;而孟子的話可以理解為“何為仁?”即仁的定義(來(lái)源)就是惻隱之心。如此說(shuō)來(lái),孟子的話是說(shuō)明仁的定義、來(lái)源,孔子的話是說(shuō)明仁的表現(xiàn)、適用范圍。“仁何為”與“何為仁”,孔孟二人的話是從不同方面對(duì)仁的規(guī)定,二人對(duì)仁的規(guī)定雖然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說(shuō)是從不同方面對(duì)仁的規(guī)定,這不同方面的規(guī)定具有互補(bǔ)性,這種互補(bǔ)性也表現(xiàn)為二者之間的一致性;孔子雖然多次提到仁,但并沒(méi)有給出一個(gè)明確的定義,孟子給出了仁的定義,這多少是對(duì)孔子思想的補(bǔ)充和豐富。孔子講“仁者愛(ài)人”,自己的親人當(dāng)然是自己親愛(ài)的首要對(duì)象(但未必是唯一對(duì)像);孟子的惻隱之心作為一種本能的愛(ài)、當(dāng)然首先反映在親人之中(但也未必完全局限于親人之中)。由此,孔孟二人對(duì)仁的不同規(guī)定在結(jié)構(gòu)上當(dāng)然有很大的重合性、互補(bǔ)性。
然而另一方面,“仁何為”與“何為仁”畢竟是兩個(gè)問(wèn)題,二者的側(cè)重有所不同,不能把二人對(duì)仁的規(guī)定簡(jiǎn)單等同;并且,孔孟二人對(duì)仁的規(guī)定雖然在結(jié)構(gòu)上有互補(bǔ)性、但并不意味著在內(nèi)容上能夠完全互補(bǔ);孔孟二人在仁的內(nèi)容上,在表現(xiàn)為一定重合的同時(shí)也有重要差異。孔子的“仁者愛(ài)人”雖然沒(méi)有考察仁的來(lái)源、定義,但卻明確規(guī)定要“愛(ài)人”,這種愛(ài)人當(dāng)然不局限在自己的親人范圍[1],這在孔子這里就表現(xiàn)為“泛愛(ài)眾”、“博施于民而能濟(jì)眾”、“修己以安人”等等;這說(shuō)明在孔子這里,仁的表現(xiàn)范圍是很廣的、絕不限于自然血緣親情。如孔子雖然講孝悌,但也講超越手足的“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如孔子雖然重故土,但也有“欲居九夷”;如孔子雖然看到自然親情的“直”、但亦看到了社會(huì)“禮”的節(jié)制,“克己復(fù)禮為仁”、“直而無(wú)禮則絞”、“好直不好學(xué),其蔽也絞”。絞即尖刻傷人、當(dāng)然要受到禮的節(jié)制,即自然的“直”要受到社會(huì)的“禮”的節(jié)制。可以說(shuō),孔子的仁雖然涉及到自然血緣、自然親情、自然地域等等自然因素,但絕不局限于這些自然因素,而是有著更為廣闊的社會(huì)性的表現(xiàn)范圍;這種表現(xiàn)范圍就表現(xiàn)為對(duì)他人的積極開(kāi)放,甚至為了他人而“克己”的合理精神;孔子對(duì)自然性的超越有利于對(duì)整體、對(duì)社會(huì)的維護(hù),從而表現(xiàn)為重整體、重社會(huì)的特征。或者說(shuō),不管是對(duì)于自己、自己家人,還是對(duì)他人、他人家人、甚至外邦人,孔子都表現(xiàn)出了以一貫的、合理的道德原則來(lái)與之交往的良好態(tài)度,這表現(xiàn)為“居處恭,執(zhí)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孔子的這種態(tài)度表現(xiàn)了他以道德理性的態(tài)度來(lái)對(duì)待一切人的正確態(tài)度,其中貫穿的是道德理性;道德理性是人與人進(jìn)行交往的基本原則,這既體現(xiàn)了道德理性的優(yōu)先,也顯示出了對(duì)自然因素的超越。對(duì)于自然地域,常人大多看到了其優(yōu)點(diǎn),孔子也有對(duì)故土的眷戀,但孔子的深刻在于還看到了自然地域的局限,“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僅僅滿足于、局限于自然地域顯然并不利于道德的合理展開(kāi),在這一方面,孟子的局限顯示出他與孔子有一定差距。對(duì)于自然親情,孟子在家中是“以情為正”,“情為正”就難免對(duì)理有所損害;孟子講“父子不責(zé)善”,善還要讓位于父子之情,而孔子則是“不學(xué)禮,無(wú)以立”、“事父母幾諫。”通過(guò)比較大體可以看出,孔子在家中運(yùn)行的主要是社會(huì)道德理性原則、孟子在家中運(yùn)行的則主要是自然情感至上的原則。后世如《三字經(jīng)》有“養(yǎng)不教,父之過(guò)”,說(shuō)明孟子的“父子不教”還是被調(diào)整了。對(duì)于自己的后代而言,“愛(ài)”基本上是沒(méi)有問(wèn)題的,愛(ài)不但包括“為什么愛(ài)”、而且還包括“如何愛(ài)”,其中“情感之愛(ài)”與“理性之愛(ài)”是愛(ài)的兩種形式、“合理之愛(ài)”與“無(wú)原則的愛(ài)”是愛(ài)的兩種性質(zhì);兩種形式的愛(ài)要結(jié)合起來(lái),但無(wú)疑應(yīng)以理性教導(dǎo)為主;兩種性質(zhì)的愛(ài)中無(wú)疑以“合理的愛(ài)”為正確,而“無(wú)原則的愛(ài)”則是不可取的、甚至可以說(shuō)“無(wú)原則的愛(ài)”就是不愛(ài)、至少是不會(huì)愛(ài)。“不愛(ài)”當(dāng)然是不對(duì)的、“不會(huì)愛(ài)”亦有所局限。通過(guò)比較兩種性質(zhì)的愛(ài)與愛(ài)的兩種形式,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孟子與孔子在這一問(wèn)題上的差距較明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shuō),超越孟子回歸孔子[2],也就是超越自然進(jìn)入社會(huì),即超越自然因素(自然情感、自然地域、自然血統(tǒng))進(jìn)入社會(huì)道義(禮、義、善)。
“惻隱之心仁也”是孟子試圖給仁下的一種定義,這種定義是否符合“仁”要按照孔子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審核一下。在結(jié)構(gòu)上,如同可以說(shuō)“蘋(píng)果是水果”、但是否可以說(shuō)“水果是蘋(píng)果呢?”當(dāng)然是不可以的,因?yàn)樗ㄌO(píng)果、蘋(píng)果只是水果的一部分。就惻隱之心與仁的關(guān)系而言,也是大體類似:可以說(shuō)“惻隱之心,仁也”、但不能說(shuō)“仁,惻隱之心”。由此可以較為明顯地看到,惻隱之心只是仁的部分、不是仁的全部;自然本能只是仁的部分、不是仁的全部[3];即使能說(shuō)自然本能是仁的來(lái)源和重要部分,但也肯定不能說(shuō)自然本能是仁的全部和歸宿。我們?cè)诳吹矫献訉?duì)仁的定義十分具體形象的同時(shí),也要意識(shí)到孟子對(duì)仁的定義還是非常不完整的;如果把仁僅僅當(dāng)作惻隱之心、僅僅局限于自然本能,其中的缺陷應(yīng)是很明顯的。質(zhì)言之,仁不應(yīng)該只包含自然因素(自然本能、自然親情、自然地域)、還應(yīng)該包含自然因素之外的很多社會(huì)因素;就孔子而言,孔子在很重視自然因素的同時(shí)、還表現(xiàn)出了明顯地對(duì)自然因素的超越,而孟子把仁的定義立足于自然因素、雖然反映出了仁的重要內(nèi)容、但也可能由此忽略仁還應(yīng)包括的很多其它內(nèi)容、并蘊(yùn)含有以自然因素來(lái)否定其它因素的可能;相比較而言,孔子重視自然因素、但又超越了自然因素,孟子重視自然因素、但卻不免局限于自然因素。客觀來(lái)說(shuō),仁作為道德原則,它本質(zhì)上恰恰是一種社會(huì)原則,雖然它與自然因素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但它本質(zhì)上是社會(huì)原則而不是自然原則。如果拘守于自然而不超越自然,那仁的本質(zhì)就要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而這種質(zhì)的變化,從孔子的立場(chǎng)來(lái)看,基本上是不允許的。相對(duì)而言,孟子的“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就比“惻隱之心,仁也”合理很多。就歷史而言,孔孟后來(lái)的《禮記.禮運(yùn)》講“不獨(dú)親其親,不獨(dú)子其子”,既有親愛(ài)親人的合理、又有關(guān)愛(ài)他人的合理,顯示了較為開(kāi)闊的視野。
關(guān)于自然與社會(huì),莊子提到了“天之天”和“人之天”、王夫之進(jìn)一步有所區(qū)分,馮契先生區(qū)分了“天性”與“德性”、楊國(guó)榮教授區(qū)分了“天性”與“第二天性”[4]。從較為寬泛的角度可以說(shuō),前者是自然性,后者則是社會(huì)性;他們都講到了二者之間的有機(jī)聯(lián)系,從最終結(jié)果上來(lái)說(shuō),也應(yīng)實(shí)現(xiàn)二者的結(jié)合,但無(wú)疑是社會(huì)性對(duì)自然性的超越。自然與社會(huì)之間既有一致又有不一致,其一致表現(xiàn)為有些自然性的內(nèi)容可以直接轉(zhuǎn)化為社會(huì)性;其不一致表現(xiàn)為有些自然性的內(nèi)容并不符合社會(huì)性的要求、需要在社會(huì)性的要求下進(jìn)行調(diào)整、其調(diào)整的標(biāo)準(zhǔn)應(yīng)是社會(huì)性而不是自然性。
就自然人而言,人是具體現(xiàn)實(shí)的、有理想也有局限的人;從起點(diǎn)上,人是自然人、但從歸宿上人卻是社會(huì)人;或者說(shuō)現(xiàn)實(shí)人還是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社會(huì)道德原則審查過(guò)的自然人。在由自然人向社會(huì)人的過(guò)渡中,自然人中合乎社會(huì)的部分會(huì)被認(rèn)可、鼓勵(lì)、發(fā)揚(yáng),其不符合社會(huì)原則的部分會(huì)被批評(píng)、調(diào)整、放棄。現(xiàn)實(shí)人雖然有局限、但現(xiàn)實(shí)人還是真實(shí)的人,似乎可以說(shuō),惟其有局限、甚至經(jīng)常犯錯(cuò)誤,所以他才是真實(shí)的;但另一方面,他雖然在現(xiàn)實(shí)上“是”真實(shí)的、但由于他還犯錯(cuò)誤,所以他在理論(理想)上還“不是”真實(shí)的,應(yīng)該由現(xiàn)實(shí)的有局限的真實(shí)發(fā)展、調(diào)整為理論(理想)的沒(méi)有缺陷的真實(shí);或者說(shuō),人在自然人角度生來(lái)就是“真實(shí)的”、但還未受到社會(huì)性的審查、還未完全合乎社會(huì)性的要求,按照社會(huì)性的標(biāo)準(zhǔn)、他還“未必是真實(shí)的”,只有經(jīng)過(guò)社會(huì)性的審查,合乎社會(huì)性的東西被認(rèn)可、鼓勵(lì)、發(fā)揚(yáng),而不合乎社會(huì)性的東西被批評(píng)、調(diào)整、放棄,即由“自然性的真實(shí)”、經(jīng)過(guò)社會(huì)性的審查與教化、最終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性的真實(shí)”。這一過(guò)程實(shí)質(zhì)上也就是逐步超越自然性而進(jìn)至社會(huì)性的過(guò)程。雖然這是一個(gè)漫長(zhǎng)的、艱苦的、無(wú)止境的過(guò)程,但卻是一個(gè)理論(理想)上最真實(shí)、最迫切需要的過(guò)程。自然性可以說(shuō)是真,無(wú)視自然性的真會(huì)出現(xiàn)很多虛偽之事,但自然的真還不是善、還要由真而進(jìn)至善;以真為最高原則是不完善的、是“抱殘守缺”[5],應(yīng)該超越自然之真而進(jìn)至社會(huì)之善。雖然這種努力是很困難的、需要克服很多自然局限性、需要不斷反省自我甚至經(jīng)常否定自我,但這卻是道德之善的“應(yīng)然”使然。
就仁的定義而言,由于仁本質(zhì)上是社會(huì)性的,但孟子卻給出了一個(gè)自然性的定義,其中固然有繼續(xù)擴(kuò)展、發(fā)展至社會(huì)性的可能,但也有以自然性代替、否定社會(huì)性的可能,所以我們?cè)诳吹矫献印皭烹[之心仁也”定義非常具體、生動(dòng)的同時(shí)也應(yīng)看到孟子這一定義所蘊(yùn)含的巨大風(fēng)險(xiǎn):即它有時(shí)難免會(huì)以自然因素代替、否定社會(huì)因素。自然的愛(ài)是一種具體的、真實(shí)的愛(ài),但它還是有所局限的愛(ài),它的愛(ài)與社會(huì)的愛(ài)相比還相對(duì)較小、較狹隘。自然的愛(ài)是真實(shí)的,簡(jiǎn)單否認(rèn)、無(wú)視它經(jīng)常會(huì)導(dǎo)致虛偽、虛無(wú);但它的局限、狹隘又說(shuō)明僅僅以自然之愛(ài)為全部(而無(wú)所不為)經(jīng)常會(huì)造成對(duì)社會(huì)原則的破壞、會(huì)受到社會(huì)原則的批評(píng)和制裁。如孔子講過(guò)“直”,直是率真、是真實(shí),但它最多是“真”、還不是“善”,要受到作為“善”現(xiàn)實(shí)化的“禮”的節(jié)制[6],否則“直”就會(huì)出現(xiàn)“絞”的弊端。即人的自然性要受到社會(huì)性的約束、要以社會(huì)性為最終原則、而不能以自然性為最終原則;或者說(shuō)簡(jiǎn)單任性、以自然性為最終原則難免會(huì)碰壁。孟子也說(shuō)過(guò)“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這里固然有很多原因,但至少說(shuō)明了當(dāng)自然人處于人際關(guān)系之中時(shí)是不可以簡(jiǎn)單適用自然原則、而要以社會(huì)原則為準(zhǔn)的。《孝經(jīng)》中有“不愛(ài)其親而愛(ài)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孝經(jīng).圣治》)這里首先要求現(xiàn)實(shí)中的自然人要處理好與親人的關(guān)系、因?yàn)橛H人關(guān)系是人最先遇到的關(guān)系,不處理好“先”而處理“后”的確有虛偽的嫌疑、違背了“真”的原則;違背了真的原則、就遑論什么善了。但《孝經(jīng)》還提到了“愛(ài)親者,不敢惡于人”。(《孝經(jīng).天子》)愛(ài)親(或優(yōu)先愛(ài)親)是可以的,但這并不必然包含著可以對(duì)他人有所損害;在此,愛(ài)親的自然原則不是處于“不害人(惡人)”的社會(huì)原則之上,恰恰是愛(ài)親的自然原則受到了社會(huì)原則的制約。可以說(shuō),由于仁本質(zhì)上是一種社會(huì)原則,而孟子給仁下的定義還基本上局限于自然性,這種自然性固然有繼續(xù)發(fā)展、擴(kuò)展至社會(huì)性的可能,但亦可能因其過(guò)分強(qiáng)烈的自然性而否定、阻礙社會(huì)性的最終定位。所以在看到孟子對(duì)仁定義十分具體、形象的同時(shí)、也要看到其中強(qiáng)烈的自然性所蘊(yùn)含的局限;超越孟子定義是十分必要的。
換言之,就人而言,既有情的方面、也有理的方面。牟宗三說(shuō)過(guò):“孔子講仁,這個(gè)仁不是一件事情,仁是個(gè)道理、是個(gè)生命的道理、是個(gè)原理。”[7]生命的問(wèn)題不完全是死板僵硬的理性規(guī)定、也有感情融入其間;反之,生命也不完全是感情用事、也有理性規(guī)范在起作用。真正做到亦情亦理并不容易,但遇人遇事又必須做到亦情亦理[8],這就要認(rèn)真全面思考人的問(wèn)題。關(guān)于人,不僅只有自己、也有他人;人人都自發(fā)地意識(shí)到自己是人,這是自然本能,恐怕不用教、也不會(huì)忘記;但這種自然本能還很不全面、往往沒(méi)有顧及他人也是人,而顧及他人、人人平等則是社會(huì)人的基本要求;這就要由自然本能進(jìn)到社會(huì)狀態(tài)、由天之天進(jìn)至人之天、由天性進(jìn)至德性、由第一天性進(jìn)至第二天性。自然狀態(tài)是真,社會(huì)狀態(tài)亦不是幻;自然狀態(tài)重要,社會(huì)狀態(tài)亦不能被忽略。在自然狀態(tài)人都為己、人都從自己出發(fā);而在社會(huì)狀態(tài)則要從一般人出發(fā)、從人人出發(fā)。自然狀態(tài)的人是個(gè)人、自己,社會(huì)狀態(tài)的人則是一般人、是人人。自己是人、但自己這個(gè)人還不是人的全部、加上他人才是人的全部;個(gè)人是人、但個(gè)人也不是人的全部、人人才是人的全部。僅從個(gè)人、自己出發(fā)只是部分,社會(huì)性要求我們進(jìn)到整體,這就需要我們也要顧及他人、人人。僅僅顧及自己而不顧及他人、僅僅顧及個(gè)人而不顧及人人,顯然還沒(méi)有從自然的局部狀態(tài)脫離出來(lái),也就仍然受制于自然的局部狀態(tài),由此人在社會(huì)中就必然會(huì)遇到諸多困惑、諸多苦惱。當(dāng)然,這種自然狀態(tài)不是完全沒(méi)有優(yōu)點(diǎn),它雖然是局部而非整體、是自然而非社會(huì),但它還是真實(shí)的、真誠(chéng)的,至少對(duì)自己、對(duì)個(gè)人是真實(shí)、真誠(chéng)的。這點(diǎn)真實(shí)、真誠(chéng)很重要,按照人的本性,人不能或很難無(wú)視自己、欺騙自己、否定自己,這是人的底線、也是人的局限;人可能一時(shí)欺騙他人、社會(huì),也可能永遠(yuǎn)欺騙他人、社會(huì),但基本上不會(huì)、不能欺騙自己,有時(shí)形式的、暫時(shí)的欺騙根本不能否定實(shí)質(zhì)的、永遠(yuǎn)的內(nèi)疚。人的這種自然、局部狀態(tài)雖然是不完美的,但因?yàn)樗辽偈钦鎸?shí)的、真誠(chéng)的,就需要我們?cè)谶M(jìn)入社會(huì)、整體的過(guò)程中努力保存并積極擴(kuò)展這份真實(shí)、真誠(chéng),而不是使這份真實(shí)虛假化、真誠(chéng)虛偽化;這種自然的局部狀態(tài)雖然真實(shí)、真誠(chéng),但還不完善、還需要發(fā)展,就決定了不能使這份真實(shí)、真誠(chéng)只停留在自然的局部狀態(tài)從而“抱殘守缺”、而應(yīng)按照“應(yīng)該”的要求使之進(jìn)一步發(fā)展、完善。
認(rèn)識(shí)到自然的局部狀態(tài)的局限就有助于我們超越自然局部狀態(tài)的困境,由自然進(jìn)入社會(huì)、由局部進(jìn)入整體。原先的真實(shí)、真誠(chéng)依然存在,但一時(shí)的真實(shí)、真誠(chéng)則要調(diào)整為永遠(yuǎn)的真實(shí)、真誠(chéng),只對(duì)自己的真實(shí)、真誠(chéng)也要調(diào)整為對(duì)他人的真實(shí)、真誠(chéng);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由自然進(jìn)入社會(huì)、才能真正由部分進(jìn)入整體,才能真正合乎社會(huì)、整體的要求,才能真正減少以至消除原先自然局部狀態(tài)的局限;原先的自私、高傲、嘲諷、嫉妒等不見(jiàn)了,代之以平等、寬容、理解、鼓勵(lì)。就仁而言,原先是不愛(ài)、現(xiàn)在是愛(ài),原先是小愛(ài)、現(xiàn)在是大愛(ài)。大愛(ài)無(wú)邊,恐怕說(shuō)的就是社會(huì)之愛(ài)、整體之愛(ài)。自然之愛(ài)“自然”是真實(shí)的、真誠(chéng)的,但社會(huì)之愛(ài)亦“應(yīng)該”是真實(shí)的、真誠(chéng)的;部分之愛(ài)“自然”是真實(shí)的、真誠(chéng)的,但整體之愛(ài)亦“應(yīng)該”是真實(shí)的、真誠(chéng)的。自己、個(gè)體暫時(shí)還不認(rèn)同、還不具有社會(huì)之愛(ài)、整體之愛(ài),說(shuō)明自己、個(gè)體暫時(shí)還沒(méi)有擺脫自然局部狀態(tài)的局限,沒(méi)有真正“完全”真實(shí)、真誠(chéng),這就需要我們既要反思又要學(xué)習(xí)、既要努力保持又要積極擴(kuò)展(優(yōu)點(diǎn))、既要努力克制自己(部分)又要積極克服自然(局限),從而最終實(shí)現(xiàn)由部分而進(jìn)入整體、由自然而進(jìn)入社會(huì)。
當(dāng)然,社會(huì)對(duì)于自然、整體對(duì)于部分并不是簡(jiǎn)單對(duì)立、不是完全替代。否則,雖進(jìn)入了社會(huì)卻沒(méi)有了真實(shí)、真誠(chéng),為了整體而壓抑個(gè)體,為了他人而壓抑自己,那也是沒(méi)有真正把自然與社會(huì)、部分與整體結(jié)合好,把二者結(jié)合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能畫(huà)地為牢、也不能一蹴而就。就過(guò)程而言,人很難一下子認(rèn)識(shí)到位、調(diào)整到位,在認(rèn)識(shí)、調(diào)整過(guò)程中,自然、部分的局限往往使人的言行未必完全合乎社會(huì)、整體的要求,人們對(duì)之也會(huì)采取一定的容忍態(tài)度。容忍可以理解、但可以理解并非停滯不前;容忍也有限度、不會(huì)無(wú)限度容忍,因?yàn)槿萑瘫举|(zhì)上也要合乎由自然進(jìn)入社會(huì)、由部分進(jìn)入整體的進(jìn)程。與容忍相異,人們對(duì)于認(rèn)識(shí)到自然、部分的局限并盡力加以克制、克服的言行會(huì)給與積極的贊賞,雖然這些言行也未必能完美無(wú)缺、未必會(huì)面面俱到、甚至有時(shí)也會(huì)使自然、部分受到一定抑制,但克制自己(部分)、克服自然(局限),努力向社會(huì)、整體所進(jìn)行的諸多努力還是會(huì)被人們認(rèn)可和鼓勵(lì),因?yàn)樗吘故窃谡_的方向上克服困難而積極前進(jìn)、克制局限而努力完善,這一方向顯然就是可喜的。孔子不是早就言過(guò)“與其進(jìn)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褒)其往也。”“禹,吾無(wú)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wú)間然矣!”
相對(duì)于仁定義的強(qiáng)烈自然性,孟子對(duì)“義”的定義卻沒(méi)有自然性。孟子以羞惡之心來(lái)規(guī)定義。羞惡之心雖然有時(shí)也以類似本能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但它在實(shí)質(zhì)上卻是社會(huì)道德意識(shí)而非自然本能。義不是自然本能,這表現(xiàn)為孟子在解釋仁時(shí)可以舉出人出于自然本能無(wú)條件救孺子的例子來(lái)證明惻隱之心的存在,但卻不能在解釋義時(shí),也舉出一個(gè)同樣出于自然本能的例子來(lái)證明羞惡之心的存在。對(duì)此,梁?jiǎn)⒊€有所感慨[9]。其實(shí)質(zhì)就是,對(duì)于義的證明不可能從自然因素中找到例子、因?yàn)榱x本質(zhì)上是社會(huì)因素。換一角度,如果孟子真正想使得仁與義共同成為人的本質(zhì)(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那恰恰說(shuō)明人的屬性中不止自然性、也有社會(huì)性;或者說(shuō)惟有把人的本質(zhì)定位于社會(huì)性而非自然性,才能真正使得仁與義共同成為人的本質(zhì);否則如果把人的本質(zhì)僅僅局限于自然因素,那至少義就不可能真正成為人的本質(zhì)(如義外);而如果沒(méi)有了義,孟子理論體系的特征恐怕就成了問(wèn)題。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仁與義的定義在本質(zhì)上只能是社會(huì)性而非自然性的;或者說(shuō)僅僅以自然性來(lái)界定仁有明顯局限,以自然性來(lái)界定義基本不會(huì)成功。
在孟子對(duì)仁的抽象定義中,自然性非常明顯,進(jìn)一步,在孟子給仁的現(xiàn)實(shí)作用范圍中,這種自然性更加明顯,即“仁之于父子”。“仁之于父子”與“仁者愛(ài)人”相比,其間既有聯(lián)系、又有差別。仁者愛(ài)人當(dāng)然包括父子之愛(ài)(甚至優(yōu)先父子之愛(ài))、但仁者愛(ài)人又不限于父子之愛(ài)[10]。父子之愛(ài)具有明顯的自然性、仁者愛(ài)人則具有明顯的社會(huì)性;父子之愛(ài)是部分之愛(ài)、仁者愛(ài)人是整體之愛(ài);父子之愛(ài)是具體之愛(ài)、而仁者愛(ài)人則較為抽象。仁者愛(ài)人相對(duì)較抽象、但仁者愛(ài)人涉及到整體,仁之于父子相對(duì)具體、但仁之于父子的范圍則相對(duì)小很多。孟子的“仁之于父子”既可以說(shuō)是對(duì)孔子“仁者愛(ài)人”的具體化、也可以說(shuō)是對(duì)孔子“仁者愛(ài)人”的縮小化。具體化使得道德原則易于操作、但縮小化則難免使道德原則出現(xiàn)一定狹隘化;道德原則易于操作當(dāng)然是十分必要的、但道德原則的狹隘則是會(huì)出問(wèn)題的。我們?cè)诳吹矫献印叭手诟缸印笔志唧w、形象的同時(shí),對(duì)照孔子的相關(guān)思想也要看到這一說(shuō)法的局限。
從較為寬泛的視野來(lái)看,基本早于孟子的郭店竹簡(jiǎn)《五行》中就有“愛(ài)父,其繼之愛(ài)人,仁也”,而孟子的“仁之于父子”顯然對(duì)之有所取舍(只取了其中一部分),這種取舍實(shí)際上對(duì)儒學(xué)之愛(ài)進(jìn)行了一定限制、縮小,這種限制、縮小使得孟子的個(gè)性立場(chǎng)更為突出,也使得不少相關(guān)問(wèn)題隨之出現(xiàn)。或許對(duì)孟子仁定義中如此強(qiáng)調(diào)自然性有所不滿,《莊子》提出了“虎狼,仁也”,(《莊子·天運(yùn)》)如果仁局限于自然性、或仁就是自然性,可以說(shuō)虎狼也具有仁;雖然這在某種意義可以如此說(shuō),但如果聯(lián)系儒學(xué)、特別是孟子區(qū)分人與動(dòng)物(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以突顯人才具有道德而言,這基本是不能接受的;可見(jiàn),如果把仁僅僅局限在自然性范圍內(nèi),《莊子》的懷疑、挑戰(zhàn)顯然難以合理應(yīng)對(duì)。或許看到了道家的詰難,荀子在界定人禽之異、人最為天下貴時(shí)就認(rèn)為是“義”、而不是孟子的人禽之異在于“仁義”。“水火有氣而無(wú)生,草木有生而無(wú)知,禽獸有知而無(wú)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荀子·王制》)就儒學(xué)而言,單個(gè)的仁、單個(gè)的義或復(fù)合的仁義都可以代表道德;但就自然性與社會(huì)性而言,仁與自然性有密切聯(lián)系,而義與自然性基本無(wú)關(guān)、本質(zhì)是社會(huì)性;如此荀子把人的本質(zhì)屬性界定為“義”而不是“仁義”,很可能是看到了《莊子》對(duì)仁自然性的詰難;如此荀子的界定顯然體現(xiàn)了對(duì)孟子的超越和對(duì)非儒學(xué)派的積極回應(yīng),體現(xiàn)了認(rèn)識(shí)的進(jìn)步。后世《三字經(jīng)》講“人不學(xué),不知義”,如果聯(lián)系到仁與義在自然性與社會(huì)性上的區(qū)別,顯然說(shuō)明“義”不可能是自然因素、而應(yīng)是社會(huì)因素;如果“義”是后天在社會(huì)中學(xué)習(xí)而來(lái)的,那么反觀孟子也就不可能在“義”的定義上給出一個(gè)類似“仁”出于自然本能的例子。細(xì)細(xì)體味仁與義、自然與社會(huì),其中的細(xì)微之處真是耐人尋味。
簡(jiǎn)而言之,對(duì)照孔子的“仁者愛(ài)人”,孟子的“惻隱之心仁也”和“仁之于父子”,孟子觀點(diǎn)中的自然性非常強(qiáng)烈;其中固然有由自然性而發(fā)展至社會(huì)性的可能,但的確難免有時(shí)以其強(qiáng)烈的自然性來(lái)否定、阻礙社會(huì)性的定位。如果說(shuō)在自然性與社會(huì)性一致時(shí),明顯自然性立場(chǎng)的局限性不會(huì)產(chǎn)生很大問(wèn)題的話,那么在自然性與社會(huì)性不一致、發(fā)生不可得兼的矛盾時(shí),過(guò)分強(qiáng)烈的自然性當(dāng)然會(huì)以自然性來(lái)否定、阻礙社會(huì)性,這也會(huì)在事實(shí)上走上人應(yīng)是社會(huì)人的另一面、即在事實(shí)上認(rèn)為人是自然人了。這自然難免在事實(shí)上出現(xiàn)拋棄儒學(xué)社會(huì)人的定位、放棄社會(huì)人應(yīng)承擔(dān)道德責(zé)任的現(xiàn)象。自然性與社會(huì)性,二者既有一致、又有不一致;我們既要看到二者一致、使之有機(jī)結(jié)合的一面,也要看到二者不一致、應(yīng)當(dāng)以社會(huì)性超越自然性的一面。雖然這種超越有時(shí)難免要對(duì)自然性有所調(diào)整,但由于是社會(huì)道德角度的“應(yīng)當(dāng)如此”,所以它又具有了“必然如此”的命令形式。
(注:本文原發(fā)表在《同濟(j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科版 2010年第4期,今稍作調(diào)整)
注釋:
[1]“孔子所講的‘仁’是一種什么思想呢?用最簡(jiǎn)單的話說(shuō),就是‘愛(ài)人’,‘愛(ài)人’是有新義的。……它雖然沒(méi)有否定‘親親’觀念,卻走出了‘親親’觀念的狹小范圍,這就有利于人們到更廣闊的領(lǐng)域中去建立聯(lián)系。”參見(jiàn)李啟謙:“結(jié)合魯國(guó)社會(huì)的特點(diǎn)了解孔子的思想”,載于楊朝明、修建軍主編《孔子與孔門(mén)弟子研究》,濟(jì)南:齊魯書(shū)社,2004年版,第38頁(yè)。
[2]楊澤波教授提到了“回到孔子去”的觀點(diǎn)。參見(jiàn)楊澤波:《孟子與中國(guó)文化》,貴陽(yáng):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頁(yè)。
[3]“從本原上說(shuō),仁出于人的本能和情感,而義則代表人的自覺(jué)意識(shí)與理性。”“但是,問(wèn)題的關(guān)鍵就在于人的本能并不是人性的全部?jī)?nèi)容,如果沒(méi)有自覺(jué)意識(shí)與理性,人就不成其為人。”“‘仁’只是成為人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參見(jiàn)徐克謙:“孟子‘義內(nèi)’說(shuō)發(fā)微”,載于《孔子研究》,1998年4期。
[4]“和先天的稟賦有所不同,德性本質(zhì)上并非與生俱來(lái),而是獲得性的品格,但德性一旦形成,便逐漸凝化為較為穩(wěn)定的精神定勢(shì)。這種定勢(shì)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人的第二天性。”參見(jiàn)楊國(guó)榮:“道德系統(tǒng)中的德性”,載于《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2003年3期。
[5]龐樸先生指出“告子主張仁內(nèi)而不仁外,肯定愛(ài)吾弟而不愛(ài)秦弟,以及他所謂的以我為悅等等,不管它有多少歷史習(xí)慣,在當(dāng)時(shí),乃是試圖將仁愛(ài)限制在區(qū)域性范圍之內(nèi)和特殊性的水平之上,無(wú)視仁愛(ài)觀念已經(jīng)突破血緣防線的事實(shí),逆時(shí)代潮流而動(dòng)的一種抱殘守缺的行為”。參見(jiàn)龐樸:“試析仁義內(nèi)外之辨”,載于《文史哲》,2006年5期。
[6]“孔丘認(rèn)為人必須有真性情、真情實(shí)感,然后才可以有‘仁’的品質(zhì),但是,真性情,真情實(shí)感還不就是‘仁’,它是‘為仁’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其充足條件。因?yàn)檎嫘郧椤⒄媲閷?shí)感可能失于偏激,所以必須對(duì)于真性情、真情實(shí)感有所加工。好像一塊美玉,它的素質(zhì)是美的,但是還必須對(duì)它進(jìn)行琢磨,才可以成為一件完全的器物。這就是加工。”“對(duì)于人說(shuō),他的真性情、真情實(shí)感,是自然的禮物。加工是社會(huì)對(duì)于他的琢磨,加工的目的是使個(gè)人與社會(huì)相適應(yīng),不相矛盾,而相協(xié)和。琢磨的方法就是學(xué)‘禮’。”分別參見(jiàn)馮友蘭:《中國(guó)哲學(xué)史新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頁(yè)、第153—154頁(yè)。
[7]牟宗三:《中國(guó)哲學(xué)十九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頁(yè)。
[8]《韓非子.說(shuō)難》有“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筑,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cái),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這大體說(shuō)明亦情亦理最好,情感的過(guò)分突出可能會(huì)對(duì)理性有所影響;對(duì)自己家人相信自然可以,可簡(jiǎn)單到只相信自己家人亦難免出現(xiàn)不必要的尷尬。也可以看出,法家韓非子所舉的這則寓言故事對(duì)儒家(特別是孟子)過(guò)分重情、重家是有針對(duì)性的。
[9]梁?jiǎn)⒊赋觥俺嗦懵愕闹皇菒烹[,不雜一點(diǎn)私見(jiàn)。這個(gè)例確是引得好,令我們不能不承認(rèn),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可惜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就沒(méi)有舉出例來(lái)。我們覺(jué)得有些地方,即如辭讓之心,便很難解答。若能起孟子而問(wèn)之,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參見(jiàn)梁?jiǎn)⒊骸肚宕鷮W(xué)術(shù)概論.儒家哲學(xu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頁(yè)。
[10]雖然《論語(yǔ)》中有“孝悌為仁之本”,但學(xué)者何懷宏提出“仁可以說(shuō)是孝悌之本,而孝悌卻不能說(shuō)是仁之本”。參見(jiàn)何懷宏:《良心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頁(yè)。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xué)、山東政法學(xu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