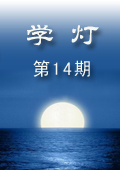
《學燈》2010年第2期(總第14期)
主 編:李銳 朱清華
周 期:季刊
出版時間:2010年4月
夷夏新辨
陳致(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華夏民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史學界對于“華夏”民族的界定有一個基本統(tǒng)一的認識。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王鐘翰的說法:“黃河中下游兩大新石器文化區(qū)系文化上的統(tǒng)一及炎黃兩昊諸部落集團的融合,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族。他們發(fā)源與興起的地區(qū)雖然不同,祖先傳說各異,而三族文化特征大體相同;他們相繼興起與建國,三代交遞,到西周已融為一體,他們是華夏族的三支主要來源”。[1]至于“華夏”觀念的形成,錢賓四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指出夏人起于今河南與山西境內(nèi),正是所謂中原華夏之地,故有夏之稱。[2]而華概念之由來,賓四先生引《國語》:“前華后河,右洛左濟,”以為“華”乃嵩岳之別稱,[3]是以“華夏”乃由地理名詞上升為文化族群觀念。現(xiàn)代語言學家則以華夏二字,均屬魚部匣紐,以為假借,華即是夏,夏即是華。由此而形成華夏一詞。
然而筆者認為“華夏”族群的形成或出現(xiàn),與“華夏”概念的產(chǎn)生當有所區(qū)別。族群的形成是自然發(fā)展的歷史過程,觀念的出現(xiàn)與成形標志著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覺。
華夏民族的出現(xiàn)或可早在虞夏之際。也就是說在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聚居在中原一帶的族群逐漸形成一共同的文化體系。然“華夏”之名,與“夷夏”觀念之分,未必就同時產(chǎn)生。其間名實之異同整合,雖以三代之悠遠,漫漶難辨。然以文獻所載,征之以近年來所出古文字數(shù)據(jù),或可管窺蠡測,以冀一得。
以姬周以來夷夏之分,尊王攘夷之觀念興,至漢而唐,歷宋而明,至遜清乃及當世,華夏民族,幾經(jīng)危殆。其間或欲師夷變?nèi)A,或曰用夏變夷,是夏非夷,抑重夷輕夏,利害得失,紛紛嘵嘵。然則究竟何者為夷,何者為夏,何為內(nèi)外之防,誠不可不辨也。
古來學者們多以為夏本為地名,所指是中原地區(qū),以禹甸舜壤,虞夏之所居。或以為殷周之際夏人仍居于河南河東一帶,故有中夏之稱。[4]然而以文獻所載看來,夏遺民最多聚居在杞繒等數(shù)小國,[5]且西周金文中有杞夷,文獻中亦時以杞為夷狄,如《左傳·僖公23年》“杞,夷也。”僖公27年又云杞桓公用夷禮朝魯。故中原諸邦國之稱為“夏”似與夏王朝夏人乃至夏地無直接關系。以文獻與金文資料來看,“諸夏”、“中夏”、“華夏”、“東夏”之名,春秋以前所罕見,且其所指與后來的華夏觀念實有不同。[6]春秋時期的“華夏”“中夏”實為宗周傾覆,平王遷都雒邑后新生的概念。故要探討“華夏”概念的來源,仍須從西周早期周人與夏的認同說起。
一、周人與夏人
“夏”與周室之間的聯(lián)系是怎么建立起來的呢?現(xiàn)代學者引用充分的史料證明周初時周人以夏人自居。然而周人與夏人在族群上是否真的有些淵源,尚在疑似之間。
我們知道周在滅商以前,曾經(jīng)是商的屬國。文獻與考古資料顯示商人對周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武丁時期始,周與商即發(fā)生了軍事上的沖突,[7]也就是說,兩者的直接接觸在武丁時期已開始。先周銅器在在受商銅器的影響。[8]張光直先生受Elman Service著名的進化模式理論的影響,[9]剖析的夏商周三代的文獻記載與考古數(shù)據(jù),認為三者可以說是共時存在的同一文化體中的不同的族群。[10]三者在不同時期內(nèi)依次取得統(tǒng)治和優(yōu)勢地位,于是形成了文獻中三代的嬗遞。周原時期周人多以商為共主,且以商之先王先公為祀主,骨文所見周王祀帝乙及成湯,又祈佑于太甲即其證。是則周人亦曾在文化上與商認同。[11]
然周與商之認同,亦有可能是周人,在尊從大邦商時期,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一種妥協(xié)政策。以文獻資料來看,周人似乎自公劉時期以降,特別是古公亶父以后,始逐漸強大。于是乎又開始尋求自己的傳統(tǒng)與文化的自主性,與殷商抗衡。
西周早期文獻中,每見周人以夏自居,如“康誥”、“君奭”、“立政”諸篇。[12]“君奭”篇中,周公對召公說:“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13]是以文王之區(qū)宇,被稱之為有夏。“康誥”中載周公對康叔封說﹕“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qū)夏”;[14]《詩·周頌·時邁》中亦有:“我求懿德,肆于時夏”的詩句。《詩經(jīng)》中也有周人稱“長夏”者,所謂“時夏”,其文例一如“時周”,[15]都是周人的自稱。在這些文句中,可以看出周人一貫以夏部族自居。
但對于周人何以自稱“夏”,學者各執(zhí)一詞。孫作云則認為周人以“夏”自居是因為“周”“夏”二族自古以來的婚姻關系,以及周居夏地。因婚姻關系而認同,恐未能必。朱東潤認為“周”本為地名,至古公亶父遷于此地,始取其地名為部族名;而“夏”則是最初的部族名,因為周人以夏之遺民自居。《左傳?昭公7年》亦載﹕“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如果詹桓伯的話可信,那么,周自后稷之世即受夏封為夏之屬地,以藩屏夏。其封地約當后來秦晉一帶,包括今陜西武功、岐山、咸陽和山西汾水之南芮城萬榮之間。[16]《國語?周語》亦曾多次追懷后稷以來的史事,如祭公謀父對周穆王說﹕“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周人之于夏,似有黍離麥秀,故國喬木之依念。
然而以夏遺民自居,未必就真是夏的遺民。如果仔細閱讀這些兩周文獻,或可測知周人以夏自居的真正原因。
“立政”篇中周公對成王說﹕“帝欽罰之(殷),乃伻(抨)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17]在這里似乎透露出周人認同于夏是出于某種政治上的需要和面對無論在文化和軍事上都出其右的大邑商時所需要的心理支持。夏之衰也,以夏桀失德,殷湯得天命以承正統(tǒng)。《書?召誥》中召公對成王說﹕“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偽孔《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18]而今殷紂失德,周以夏之遺胤自然可重新尋回天命,于是周公或召公乃對年幼的成王說:“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19]
關于周人的起源與先世,目前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大約有兩種看法。三十年代,錢賓四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中提出周人后稷所封的“邰”和公劉所居的豳都在今山西一帶,在古公亶父的時候始遷至岐山。錢說一出,學界多從之;然而,中國大陸的學界,如范文瀾、郭沫若等都認為周人源自陜甘一帶的涇渭流域。兩說都有文獻與考古資料作為依據(jù),未審何從。但是,不管周人是從什么地方發(fā)源,他們以夏的遺民自居,認同于夏文化,卻是確鑿無疑的。考古學家們?nèi)玎u衡、王克林等,也從對山西汾河中下游的晚期龍山文化、夏縣東下馮文化至西周各階段的陶器的類型特征和淵源關系的分析來證明周族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夏代文明的影響。[20]然而周人究竟是否夏人,恐怕已難窮其究竟。
但重要的是周人對夏的認同其背后的原因。我以為夏所給予周人的是一種民族自尊自信乃至自勵的某種精神支柱。特別是在面對原宗主國殷商的時候,夏是周人受天命的正統(tǒng)性的標識。以夏自居,既是神性的證明,也是世俗的需要,畢竟茫茫九州島,是禹之績,夏雖亡國,其文明與歷史的痕跡尚在。
周人以夏自居,同時也并不完全拒絕接受殷商的物質(zhì)文明的影響。種種史料表明,周初肇造,蓽路藍縷,在種種物質(zhì)、文化、制度上廣泛地接受了商文明的影響。這種接受也并非不加采擇。相反,周人在吸收商文化時亦有所保留,有所限制,使其適于實際統(tǒng)治需要。筆者在拙作“說夏與雅:周代禮樂形成與變遷的民族音樂學考察”中詳細討論了周人在吸收商代音樂文化時所經(jīng)歷的漫長和曲折的過程,周人所創(chuàng)制的雅樂及其制度在吸收晚商音樂文化的同時,也阻礙遲滯了音樂文化發(fā)展的自然連續(xù)過程,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xiàn)了周人保守和狹隘的一面。從“夏”字的字源分析以及夏樂雅樂的名實制度的研究入手,筆者在拙作中認為:
自文王至周公,周人不斷以“夏”自居,這實質(zhì)上是一種自身正統(tǒng)的證明。以夏自居,承接夏的文化傳統(tǒng),無疑能使在各方面處于劣勢的周人尋找到了一種精神上乃至政治上可以與殷人相抗的依據(jù)。從夏人那里承襲的“夏樂”也具有音樂之上的某種民族文化象征意義。正因為如此,周人在滅商以后沒有全盤接受殷人的音樂文明,相反,對后者亦有排斥的成分。也正因為如此,周初周公制禮作樂,除了承襲歷代古樂以外,更以“托古改制”的方式把歌頌武王滅商的“大武”歸入他所創(chuàng)制的禮樂。周初所用的六代樂舞中,從黃帝之“云門”,到周之“大武”,六代之舞無一不是正統(tǒng)的標識。
于是,以關中地區(qū)先周文明為溫床、夏文化為主體的“雅”文化乃取代河洛地區(qū)的殷商音樂文化轉而居于主導地位,并在有限地吸收了河洛地區(qū)音樂的基礎上創(chuàng)制并逐漸完善了以宗周為核心的禮樂制度,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西周時期的雅樂。這一過程具有典型意義的昭示了兩個相對獨立的文明以軍事征服的方式交相整合而形成的文化移植(Acculturation)現(xiàn)象。[21]以涇渭流域為中心的周民族固然有限地接受了殷商音樂文明,而另一方面,以洹水流域為中心的河洛殷民族并未融入西來的宗周音樂文化,而是隔離化(Compartmentalize)了后者。兩個文明在歸一之后,合而未整,如果套用人類學術語來說,在西周時期,涇渭地區(qū)的周民族比河洛地區(qū)的商族更為涵化(Accultured)。因此,西周時期所制訂和形成的禮樂制度其實施范圍仍以關中區(qū)域為主。而夏與正統(tǒng)的概念也僅與宗周文化相聯(lián)系。[22]
二、西周時期的夷夏觀念
(一)夏
西周時期的“夏”的觀念事實上與春秋文獻中的“夏”“諸夏”“華夏”其所指并不一致。許倬云教授在《西周史》一書曾論及西周時期的“華夏”觀念問題,他指出:
建立東都成周和在東方分封大批姬姓與姜姓諸侯配合在一起,為周王國的統(tǒng)治打下了穩(wěn)固的基礎。這個基礎上,不但有姬姜的宗族控制了戰(zhàn)略要地,更在于經(jīng)過一番調(diào)整,周人與東土的部族揉合成為一個文化體系與政治秩序下的國族。殷商自稱大邑,卻無“華夏”的觀念。這些周王國內(nèi)的各封國,自號華夏,成為當時的主干民族。[23]
許教授在此精辟地指出了商周在文化族群認同上的根本分別,周人以“華夏”的概念來稱呼周人以及周初囊入版圖的東土部族,顯然優(yōu)于商人以“大邑”自居坐大的文化策略。然而我認為許先生此說在時間上似將“華夏”概念的形成在西周可說是始露其端倪。周王國內(nèi)的各封國自號華夏,仔細梳理起來,尚缺少足夠的證據(jù)說明,主要是西周時期的夏的概念,與春秋時期的夏并非盡同。周初文獻中所見的“夏”、“時夏”、“區(qū)夏”、“方夏”與“有夏”所指無一例外地是文王所開辟的區(qū)宇。在地理上是指宗周所在的關中地區(qū)周人的中心區(qū)域,與故殷之宇甸相對舉;文化上標示著宗周的文明與制度,亦與故殷相頡抗。
(二)“中國”和“殷國”
以地理概念而論,彝器如武王成王時期的康侯簋銘云:“王朿伐商邑,令康侯啚(鄙)于衛(wèi)。”紂子武庚治下的衛(wèi)被稱為“商邑”自不待言。保尊保卣銘文則曰:“乙卯,王令保及殷東或(國)五侯。”此殷東國固指今山東境內(nèi)的“反殷”,商奄、蒲姑等邦國。而中原各國則在周代仍被稱之為“殷國”。《周禮·秋官·大行人》載: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遍存,三歲遍眺,五歲遍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xié)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jié)、同度量、成牢禮、同數(shù)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24]
以周之幅員廣闊,天子如“歲遍存”邦國諸侯,幾無可能。所以王所歲存者,必其近畿內(nèi)的邦國諸侯。至若十二年巡狩的“殷國”,當然是《書·酒誥》中的“殷國”,所指是襲殷之故地,大量居住著殷遺的中原姬姜及他姓諸侯。[25] 《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西周時中原地區(qū)各國,以殷之舊邦,或稱之為“殷國”“商邑”,或與東國南國淮夷等相對而言,稱之為“中國”“內(nèi)國”。而與宗周相對而言,則亦可稱“東國”。《書·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又云:“惟乃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qū)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是以區(qū)夏即西土,故殷之畛域亦曰東國。[26]“夏”與“中國”相對舉,如武王成王時器何尊銘文曰:“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今宅茲中或(國)”。[27]銘文所說的“中國”顯然是指武王克殷以后,所厎定的殷的畿甸。《詩經(jīng)·大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此“中國”觀念與前舉何尊銘文一樣,也并不包涵周所居之夏,即宗周一帶。故自晚商至西周時期,“中國”與“夏”兩詞所指不同,前者是殷之舊地中原地區(qū),后者是周之故封關中自岐周至宗周一帶。胡厚宣認為,卜辭中有“中商”一辭,與東南西北四方神并舉,即“中國”稱謂之起源,如后世所謂“中國、夷、狄、戎、狄”“五方之民”(《禮記·王制》)。[28]案卜辭中“中商”一詞,見于姚孝燧《殷墟甲骨刻辭類纂》者凡三例:[29]
| 1 | 《合集》07837 | …勿于中商。 |
| 2 | 《合集》20453 | □巳卜,王,貞于中商乎…方。 |
| 3 | 《合集》20587 | 庚辰卜,中商。 |
| 4 | 《合集》20650 | 戊寅卜,王,貞受中商年。…月。 |
用香港中文大學漢達文庫檢索共有六例,其文如下:
| 1 | H07837 | 勿于中商。一 |
| 2 | H20453 | (1)□巳卜,王,貞于中商乎〔 〕方。 |
| 3 | H20454 | (1)□巳卜,王,貞于中商乎〔 〕方。 |
| 4 | H20540 | (1)己酉〔卜〕,貞王于中商。 |
| 5 | H20587 | 己酉〔卜〕,貞王 于中商。 |
| 6 | H20650 | (3)戊寅卜,王,貞受中商年。十月。 |
其中例2例3重出,誤,《甲骨文合集》20454條,其文實異。以所列詞例來看,中商為殷商畿甸內(nèi)一地名,應無問題。例4云:“己酉〔卜〕,貞王(省)于中商。”足資為證。胡厚宣氏以為:“中商即商也,中商而與東西南北并貞,則殷代已有中東西南北五方之觀念明矣。”卜辭中“中商”而與東西南北并舉,則“中商”當指商之都邑。康王時器彔 卣銘云:“王令 曰:淮夷敢伐內(nèi)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蚌。”故所謂“中國”也稱“內(nèi)國”。卜辭中固有“東土”(《合集》7084、7308)“西土”(《合集》6357、7082、9741正、17397正、20628、36975,《屯南》1049)“南土”(《合集》896、20576正、20627、36975)“北土”(《合集》8783、33049、33050、33205、36975)之稱,實皆非方國名。《合集》36975甲骨文曰:“己巳王卜貞…歲商受…王卜曰吉,東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6甲骨文曰:“乙未卜貞今歲受年,不受年,南受年,東受年。”與此“四方”“四土”“四國”的觀念相對舉,殷人很可能已經(jīng)有了“中國”的概念,但此“中國”所指是指殷商統(tǒng)治的中心區(qū)域。誠如田倩君所指出的:“‘中國’也是個相對稱謂,當開始命名為中國時,在它的周圍一定有許多方國,即所謂四夷存在著。‘中國’這個稱號并非我國所獨有,其它國家也有作此稱呼的。”[30]文中并引章太炎《章氏叢書》:
印度稱摩迦陀為中國;日本稱山陽為中國。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土中以對邊郡,舉領域以對異邦。[31]
以此視之,所謂“中國”,其初殆如中商之概念,特與四方、四土相對舉,并非特定的地理概念和國家民族概念。
王爾敏統(tǒng)計先秦古籍中出現(xiàn)“中國”一詞,指出其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含意約有五類:其中謂京師之意,凡9次;謂國境之內(nèi)之意,凡17次;謂諸夏之領域,凡145次;中等之國之意,凡6次;中央之國之意,凡1次。[32]王所做的統(tǒng)計并非精確,特別是他說的第五類中央之國之意,所舉的例證為《列子?湯問》“南國之人祝發(fā)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在這里,中國既是中央之國的意思,也是指中原諸國,即諸夏之領域。且《列子》是否晉人張湛所偽托,仍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是從這些例證來看,用作京師之意者多見于詩書中的較早(西周時期)的篇章,指諸夏之領域者始見于春秋時期的文獻。所以就地域而言,西周之宇內(nèi)有夏、中國、四夷之分,而非夷夏之分。
(三)西周夷夏亦是階級之分
西周銅器銘文中周畿內(nèi)之民被劃分為相對舉的不同類別。如李零就注意到:“西周金文中的居民有國野之分和夷夏之分,國人叫邑人,野人叫奠人;周族叫‘王人’,外族則稱‘夷’。”[33]這一點非常值得重視。周初的商周戰(zhàn)爭,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分封、殖民、移民和流徙的社會調(diào)整和變動,造成了族群混雜融合的局面。西周銅器中保留了被稱為“夷”的族群的名稱。如我們所熟知的淮夷、[34]南夷[35]和東夷[36]等自不必說,另有杞夷、舟夷、[37]西門夷[38]夷、[39]秦夷、[40]京夷[41]與畀身夷[42]等,其總稱曰諸夷。[43]這些西周諸夷,除了自商代以來就有的淮夷、南夷、東夷之外,其它諸夷在東周文獻中,便已銷聲匿跡。從西周晚期的詢簋與師酉簋銘文來看,這些諸夷事實上與周人雜處,并且有的在周王朝中擔任一些職務。如師酉簋銘文云:
王乎史墻冊命師酉:“司乃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夷、夷、秦夷、京夷、畀身夷……”[44]
詢簋銘文云:
“今余命女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門夷、秦夷、京夷、夷;師笭側新:口華夷、畀身夷、鵌人;成周走亞:戍秦人、降人、服夷……”[45]
兩器銘文都顯示這些夷人在周王朝中擔任著虎臣一職務,在西周戶籍或人口分類中屬于“邑人”一類。
所謂邑人在西周金文大約指一些周兩京(宗周、成周)之外的城市人口。白川靜以為邑人即國人,指周代的城市居民。然而國與邑從語義上來看,有重要與次要,大與小,都與城,周與非周之異。文獻中的國人似以宗周與成周地區(qū)的周人為主要對象。而諸夷所屬的邑人身分當是周人以外的其它城邑的居民。似此華夷雜處的現(xiàn)象事實上,非自周始。李濟之先生就曾指出安陽殷虛所發(fā)現(xiàn)的人骨中,有一些具有明顯不同的體質(zhì)特征。然自宗姬氏由西方崛起,短短數(shù)十年內(nèi)乃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又經(jīng)歷了短短的數(shù)十年,乃至西進滅商、建侯衛(wèi)、伐反殷,東平淮徐,南征江漢,北抵燕遼,其所依賴的統(tǒng)治術,除了分封宗親勛舊之外,還包括姬周族人的武裝殖民。《詩經(jīng)》中每言“西方美人”“西人之子”,殆即居東的周貴族或周民之后裔。
另外一項措施就是周王朝的移民政策。周人的移民政策包括三種情形,一是上面所說的周人的殖民和移民,銅器中宜侯?簋中有所謂“在宜王人”即周的移民。
其次是商遺民的遷徙。滅商和平定武庚、淮徐亂后,首先是大批的殷遺,周人稱之為殷多士,遷入周的直接統(tǒng)治區(qū)域,這包括新建的洛邑,成周,甚至到周的中心岐周宗周地區(qū)。近年來陜西周原出土的大量殷遺民的青銅器,如微史家族銅器等足以為證。見于文獻的殷遺有遷于魯?shù)囊竺窳澹唬簵l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于衛(wèi)的殷民七族,曰: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徙入唐的有所謂懷姓九宗。
此外,另一項重要的而為我們所忽略的移民政策是在周兩京和畿甸以內(nèi),遷入或利用其它的非商非周的族裔族群。我認為金文所見的西門、杞、秦、京、畀身、舟諸夷即是這樣一些人物。這些所謂諸夷未必是在體質(zhì)上異于殷周的周邊民族,以詢簋、師酉簋及史密簋的銘文看來,西門、畀身、□華、服夷固無可考,杞、京、秦、舟諸夷皆可測知。其中秦之稱,固無可怪,因秦雖嬴姓,屬東方風偃族群,然自非子以后雜處于涇渭戎狄之間,周人或以是目之為夷。杞則夏之族裔,是殷求夏后,始居于杞,武王滅商,立為諸侯者,此為正牌的“夏”,稱之為夷,殊為怪事。京于金文與《詩》《書》中多指周之兩京,唐蘭考釋令彝,以為詩書中的京或為鎬京內(nèi)的京室(京太室),或為成周之京宮。[46]所謂京夷殆指兩京中所居住的其它族胤。至于舟夷,學者們一般認為舟乃州之音假。此州乃姜姓諸侯國,領地在今山東安丘。[47]故在西周人的觀念中,宇內(nèi)之民以族群論,可分為三種,一曰周人、王人、里人,是姬周族人貴族及其屬下的周平民,一曰殷人、殷民、眾殷、庶殷、殷多士,乃指殷之貴族聚落,多數(shù)散布在中原各諸侯國,特別是成周洛邑、宋、魯、衛(wèi)、鄭、晉等國。三曰諸夷、夷人、邑人,其來源為周初的非殷非周的各邦國族群,其中很多移居周城邑內(nèi)。宜侯?銘文中有所謂“邦司”“夷司”。前者所司“自馭至于庶人。”后者所司為外土遷入的非周族移民,即所謂諸夷。
至于諸夷的地位在三類人中可說是最低的。殷商舊族因周人統(tǒng)治需要受到相當?shù)亩Y遇,自冢宰卿士以下,祝宗卜史之職多有殷遺出任。宋、魯、鄭、衛(wèi)、晉各國的殷遺也有相當?shù)牡匚弧O啾戎拢T夷的地位要低得多,從彝銘來看,其地位不過是虎臣一類衛(wèi)士,或如靜簋銘文中所述充任宮廷仆役(丁卯,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服小臣尸仆學射)。詢簋銘中的服夷與所謂降人、戍秦人略同。[48]又有夷臣等身分大約是當時充任貴族家中廝養(yǎng)一類的夷人。夷人也有一族一族被周天子賞賜臣下或諸侯的。如西周井(邢)侯簋云:“隹三月,王令榮內(nèi)史曰:(割)井(邢)侯服,易(钖)臣三品:州人、倲人、墉人。”[49]中方鼎云:“王令太史兄(貺)衤鬲土。王曰:‘中,茲衤鬲人入史(事),易(錫)于珷(武)王作臣,今兄(貺)畀女(汝)衤鬲土,作乃采’”此處中是人名,武王因衤鬲人入事于周,因功封中于衤鬲土并其地之人民,曰衤鬲人。[50]
西周觀念中的人群,可以下三方面來分:
| ? | 城邑 | ? | 鄉(xiāng)野 |
| 地理名詞 | 國、邑、邦 | ? | 野、甸 |
| 人群名詞 | 國人、邑人、邦人 | ? | 奠(甸)人、野人 |
| ? | 周族 | 異族 | 商族 |
| 族名 | 王人[51]、周人 | 夷、夷臣、夷人 | 殷、殷人、殷民、庶殷、殷多士 |
| 政治名詞 | 周之都邑 | ? | 其它諸侯城邦都邑 |
| ? | 國人 | ? | 邑人 |
1)就地理觀念而言: 城邑 vs. 鄉(xiāng)野
國、邑、邦 vs. 野、甸
國人、邑人、邦人 vs. 奠(甸)人、野人
2)就族群族屬而言: 周族 異族 商族
王人、周人 夷、夷臣 殷、殷人、殷民、 庶殷、殷多士
3)就政治上而言: 周之都邑 vs. 其它諸侯城邦都邑
國人 vs. 邑人
故所謂夷夏之分在西周時期有著明顯不同的概念和界定標準。在這個標準的背后潛含著狹義嚴格的族群優(yōu)勢和歧視心理。所謂“夏”,就地理而言指歧周宗周一帶,姬周一族的源地,這一觀念一直延續(xù)至于關中地區(qū)代周而起的秦。《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魯觀樂,至《秦風》乃贊道:“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其周之舊乎?”至秦王朝建立,在秦律法中秦地仍以夏名之,秦始皇帝13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云:“臣邦人不安秦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可(何)謂夏,欲去秦屬是謂夏。”[52]可見,宗周舊基,秦之屬地,至秦一統(tǒng)宇內(nèi)仍襲周之舊稱,以夏自居。而戰(zhàn)國晚期蘇秦說齊王,謂“秦雖強,終不敢出塞流河,絕中國而功(攻)齊。”[53]秦人稱秦地為夏,是延用西周時的舊稱,蘇秦所說的“中國”是中夏諸國,也是延用舊稱,其范圍并不包秦齊楚等國。
另就人群而言,夏指所謂王人周人西方之人,西周貴族故每有“伯夏父”、“仲夏父”“安夏父”之名,以自高貴。夷則指殖民地的族群聚落,周固有城邑中的外來移民,以及邊裔之異族族群。再有從政治上說,則夏是宗周文明制度的標識,其文化內(nèi)涵是周初至西周中葉所逐漸形成的以周文明為主體,大量吸收商文化的一套禮儀、典章和制度。
而夷的觀念在西周時期大約有三層涵義。一是作為集合名詞,文獻與金文資料中,有所謂“蠻夷”、“夷狄”、“諸夷”、“三夷”、“四夷”、“九夷”等自是化外宇內(nèi)異族之統(tǒng)稱,又有“南夷”、“北夷”、“東夷”、“西夷”、及“淮夷”、“島夷”、“風夷”、“畎夷”、“赤夷”、“白夷”、“黃夷”、“藍夷”等則某類特定族群之統(tǒng)稱,或以地域名,或以族姓名,或以其它特征名。
其次則為專有名詞,特指某一族,如前文述及金文中之杞夷、京夷、秦夷、及文獻中所見之徐夷、萊夷、莒夷、邾、吳等等至春秋時期仍時常被稱之為夷。
三曰周宇內(nèi)某種身份人之代稱,其如前所述之杞夷、京夷、秦夷等,既是族名,也是徙居后的身份,此外另有西門夷、服夷、畀身夷、夷人、夷仆、夷臣、諸夷等也標識著其社會地位與身分。師詢簋銘文中記載周王“睗(賜)女(師詢)矩鬯一卣圭瓚夷□三百人。”夷后疑為仆字。
所以說西周時期的夷夏之分,在地理與民族概念上既非春秋的“中國”與周邊民族之分,文化上也絕非春秋以后的“華夏”與“夷狄”之分。從以上研究看來,西周觀念中的“夏”無論從地域,還是從文化、種族上來說,都相對來說比較狹隘,并未上升到如顧立雅教授所說的“文化”“禮俗”上認同的高度。真正的文化禮俗上的夷夏之分乃在春秋時代。
東夷、淮夷、南夷和南淮夷商代已存在,骨文中又有夷方(《甲骨文合集》33038,33039)或徑稱“夷”(《甲骨文合集》6457,6458,6459,6460,6461,6462),自武丁時期起即與商時有征伐之事。此邊裔諸夷在西周時依然存在,且時與周為敵。以金文所記而言:
| 西周初 | 隹王來正尸(夷)方 | 小臣艅犧尊 |
| 周公 | 隹周公弙征伐東尸(夷) | 周公東征鼎 |
| 成王 | 王令遣截東反夷 | 疐鼎 |
| 成王 | 東夷大反白懋父殷八師征東夷 | 小臣言逨簋 |
| 西周早 | 隹公大保來伐反夷年 | 旅鼎 |
| 西周早 | 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貫行 | 中方鼎 |
| 西周早 | 隹王伐東夷 | 鼎 |
| 西周早 | 隹王既尞厥伐東夷 | 保員簋 |
| 西周中 | 王令 |
彔 |
| 西周中 | 隹白屖父 成即東命戍南夷 | 競卣 |
| 西周中 | 周白邊及仲偯父伐南淮夷俘金 | 仲偯父鼎 |
| 西周中 | 王令師俗史密曰東征敆南夷膚虎會杞夷舟夷雚 不折廣伐東或 |
史密簋 |
| 昭王 | 南國 子之叛,南夷東夷具見 | 宗周鐘 |
| 懿王 | 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 | 無 簋 |
| 西周晚 厲王 |
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 | 虢仲盨 |
| 夷厲 | 南淮夷遱殳內(nèi)伐 | 敔簋 |
| 夷厲 | 淮夷舊我員畮臣今敢博眾叚反厥工吏弗跡我東或 今余肇令女率齊帀 萊秂屃左右虎臣正淮夷 |
師寰簋 |
| 宣王 | 克狄淮夷 | 曾白簠 |
| 宣王 | 至于南淮夷 | 兮甲盤 |
| 西周晚 | 南中邦父命駒父即南者侯率高父見南淮夷氒 取氒服堇夷俗 |
駒父盨蓋 |
| 西周晚 | 南或 子敢臽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撲伐氒都 子 乃遣閑來逆邵王南夷東夷具見 |
鐘 |
可見終西周之世,周與淮夷東夷南夷的征戰(zhàn)無時或斷。金文辭輔之以文獻記載,可知成王時周公召公的東征南征自不必說,昭王南征荊蠻,喪六師于漢,起因似與淮夷之伐內(nèi)國有關。《后漢書·東夷傳》又載穆王時徐戎(夷)率九夷犯宗周。[54]《漢書?匈奴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55]夷厲時期,淮夷亦曾入寇,周王遣虢仲伐之。迨宣王立,召虎平定淮夷,方叔遠征荊蠻程伯休父伐徐方,周與周邊諸夷的軍事沖突,愈演愈烈,而西夷、諸戎、諸羌等又近在關中王畿左邇,時有征伐。《今本竹書紀年》載:懿王七年,西戎侵鎬。十三年,翟人侵岐。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十三年,翟人侵岐。宗周既隕,不但周王室被迫東遷以避戎患,周在關中一帶的直屬邦國,也隨之而東。
故所謂春秋時期夷夏觀念的產(chǎn)生,實因華夷雜處、夷患愈演愈熾,周人窮于應付有關。劉申叔先生雖囿于當時所具備的考古與其它數(shù)據(jù),已見及此。申叔先生指出:
殷商既興,四夷向化,“王會”所言,歷歷可考。又據(jù)《紀年》一書,則殷商中葉有西戎(太戊26年),九夷(太戊61年),侁人(河亶甲五年)之來賓,有藍夷(仲丁六年)之征討。地望所在,渺不可稽。惟據(jù)《詩》《書》及《史記》《紀年》考之,知殷人與異族之關系,僅有二端。一為武丁時漢族辟地于西南,一為武丁后,異族蔓延于西北-……(迨及周世)關內(nèi)河東已開華夷雜居之漸矣。觀《孟子》言狄入攻亶父,《詩》言南仲伐昆夷,則豐鎬以西,久罹戎患,得季歷文王以征之,而戎狄之禍稍弭,不然,驪山之禍,不待周末而發(fā)矣。[56]
儀征劉申叔先生,所著《中國民族志》論夏殷之形勢及西周與異族之關系,雖囿于當時資料,然以文獻所載,洞燭微隱,誠多不刊之論。惟西周中晚期夷狄之患,實與周人對四夷與諸夷的統(tǒng)治政策有關。周初廣魯天下,封建諸侯,同時對殷商舊族采取了懷柔安撫政策,在具體實施上是成功的。然對四夷和諸夷,似采取了較強硬的措施,在民族政策上,自稱周人王人,以夏自居,以別于庶殷諸夷,洵為取敗原由之一。
三、春秋時期的夷夏觀念
西周華夷雜處最終使王朝變生肘腋,直至幽王舉烽,申戎、繒、西夷、犬戎直搗宗周,西周國祚就此以終。然而平王東遷,定都雒邑之后,周人的中心統(tǒng)治區(qū)域隨著周王室轉移到中原地區(qū),此時夏的觀念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筆者在拙文“說夏與雅:宗周禮樂形成與變遷的民族音樂學考察”中提出:
平王東遷之后,“夏”的概念始被擴大到廣大中原地區(qū),也就是《左傳》與《國語》中所常見的“諸夏”。這個諸夏就是“晉主夏盟”的“夏”。它所包含的范圍已不光是王畿以內(nèi),而是囊括了名義上尊奉周天子的中夏各諸侯國,春秋時期的霸權之爭和尊王攘夷觀念都是以這個新的諸夏觀念為核心的。與“夏”的概念相對應的是“雅”的概念,原來與宗周文化和關中地區(qū)文明相聯(lián)系的“雅”至此也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與先王與宗周相聯(lián)系的雅文化,在東周建立之后,當然為東周王室所據(jù)有,雅的概念由此而附著在新的統(tǒng)治群上以確立其正統(tǒng)性,于是先王與后王,宗周與東周,就文化而言變成了二而一的事物。這一個觀念上的變化在后人的表述中更為明確。《荀子》曾提到﹕“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后王謂之不雅。”(“王制篇第九”)荀子還一再談到“法后王、一制度”的“雅儒”這一種人物。《毛詩序》也說﹕“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57]所謂“變雅”和“不雅”顯然都是指與周王道相悖離的事物。而雅就是周的王道,即先王與后王、宗周與東周的統(tǒng)一體,也是“古雅”和“雅正”的統(tǒng)一體。[58]
這一變化,從本質(zhì)上說是姬周文明與中原殷商舊族的再度融合。其根本的標志是此時周人的“夏”觀念已不復與“中國”相對舉,而是整合為一。由是出現(xiàn)“諸夏”“華夏”“東夏”等概念。這表現(xiàn)了周人在文化上的包容和變通精神。許倬云教授在談到周文化的包容性時指出:
“華夏”變成周人用來稱呼整個的族群,不過他并不叫它“周”,因為他承認有別處不是周,這種精神很了不起,使得中華民族可以成型……所以我們說中華文化的統(tǒng)一性比政治的統(tǒng)一性先出現(xiàn),而且維持的時間相當長,等到周人強大的文化包容性與政治包容性出現(xiàn)以后,才造成了一個真正統(tǒng)一的政治秩序。[59]
“夏”與“中國”在春秋時期皆指中原地區(qū)以姬姜為主,居住著大量殷遺的各諸侯邦國。伴隨著一統(tǒng)觀念的形成,此地理文化概念乃逐漸形成為民族認同的“華夏”概念。顧立雅曾指出:
所謂“華夏”概念的基準自古以來都是文化上的。中國人有其獨特的生活,獨特的實踐文化體系,或冠之以“禮”。合乎這種生活方式的族群,則稱為“中華民族”……這是一個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過程,變夷為夏,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偉大主干。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of “Chinese-ness,” anciently and throughout history, has been cultural. The Chinese have had a particular way of life, a particular complex of usages, sometimes characterized as li 禮 (ritual). Groups that conformed to this way of life were, generally, considered Chinese….It was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transforming barbarians into Chinese, that created the great bulk of the Chinese people.[60]
兩周時期“夏”與“中國”的觀念的發(fā)展變化恰如顧立雅所描述的那樣。隨著多族群的接觸、交流、沖撞與整合,夷夏之分野也時有變化。正是這種文化上的包容和涵蓋特質(zhì),使中華文明經(jīng)百劫而不衰,歷千祀而不絕。
許倬云和顧立雅兩先生談到的周人“華夏”觀念的這種包容性,可謂精確不刊。然而我認為周人“華夏”觀念的形成,不應該否認有其被動的一面,從西周的以夏自居,到春秋的包容諸夏,以及夷夏之分,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基于周人在華夷雜處,王室播遷之后所產(chǎn)生的憂患意識。自王室東遷以后,蠻夷戎狄之患,并未稍戢,相反,可以說終春秋之世,無時或無。[61]
顧棟高據(jù)《春秋》經(jīng)傳所記,分戎之別為七:有驪戎(在今陜西驪山附近)、犬戎(在今陜西鳳翔)、陸渾之戎(本處瓜州,即今燉煌,曰允姓之戎,遷于中國曰陸渾之戎,在今河南嵩縣,又名陰戎,封晉之陰地,其支又名九州島戎、小戎、姜戎)、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在今河南伊洛一帶)、蠻氏之戎(又名茅戎,居解州之平陸)、北戎(又名山戎,在永平,今北京河北一帶)、戎州己氏之戎(《春秋》經(jīng)直曰戎,或言即徐戎)。狄之別有三:曰赤狄、白狄、長狄。赤狄又分六族:東山皋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鐸辰。白狄又分三支:鮮虞、肥、鼓。東方之夷曰萊、介、根牟。又有自殷以來稱盛的淮夷。南方則有群蠻、百濮(夷之一支)、盧戎(戎之一支)。[62]從《春秋》經(jīng)傳所載來看,華夷雜處的局面,春秋時尤烈。華夷雜處,有散居,有群居。群居者又時與中原諸夏離析整合。離則依附,聚則為患。依附則歸化為民,或為所用,為患則滋擾中國,至于國滅祀絕。見于經(jīng)傳者,其例如:隱公7年(-716),戎州己氏之戎伐凡伯,隱公7年(-716),北戎侵鄭,桓公6年(-706),北戎侵齊,莊公18年(-676),己氏之戎入魯境,莊公24年(-670),己氏之戎侵曹,莊公26年(-668),莊公伐戎,莊公28年(-666),晉伐驪戎,莊公30年(-664),山戎病燕,齊伐之,莊公32年(-662)冬,赤狄伐邢,閔公2年(-660),赤狄入衛(wèi),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閔公2年(-660),虢公敗犬戎于渭汭,僖公元年(-659),邢避狄遷于夷儀,僖公2年(-658),虢公敗犬戎于桑田,僖公8年(-652),赤狄伐晉,僖公10年(-650),赤狄滅溫,溫子奔衛(wèi),僖公10年(-650),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12年(-648),齊管仲平戎于王,僖公12年(-648),諸侯城衛(wèi)楚丘之郛以防狄,僖公13年(-647),赤狄侵衛(wèi),僖公13年(-647),淮夷病杞,僖公14年(-646),赤狄侵鄭,僖公16年(-644)秋,赤狄侵晉,僖公16年(-644),王子帶召揚、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僖公16年(-644),王以戎難告于齊,僖公18年(-642)五月,宋襄公伐齊,狄救之,冬,邢人狄人伐衛(wèi)。僖公20年(-640),赤狄、齊人盟于邢,僖公21年(-639),赤狄侵衛(wèi),僖公22年(-638),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僖公24年(-636),赤狄伐鄭,僖公30(-630)秋,介人侵蕭,僖公30年(-630),赤狄侵齊,僖公31年(-629),赤狄圍衛(wèi),僖公32年(-628),衛(wèi)人侵狄,旋與盟,僖公33年(-627)夏,赤狄侵齊,秋,赤狄伐晉,僖公33年(-627),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文公4年(-623)夏,赤狄侵齊,文公7年(-620)夏,赤狄侵魯西鄙,文公8年(-619),伊雒之戎將伐魯,文公9年(-618)夏,赤狄伐齊,文公10年(-617)冬,赤狄侵宋,文公11年(-616)秋,赤狄侵齊,文公13年(-614)冬,赤狄侵衛(wèi),文公17年(-610),周甘歜敗蠻氏之戎于邥垂,宣公3年(-606)秋,赤狄侵齊,宣公5年(-604)夏,赤狄侵齊,宣公六年(-603),赤狄伐晉,宣公7年(-602)秋,赤狄侵晉。宣公7年(-602)夏,魯公會齊侯伐萊,宣公8年(-601)夏,晉師、白狄伐秦,宣公9年(-600)夏,齊侯伐萊,宣公9年(-600),魯公取根牟。宣公15年(-594),晉師滅赤狄潞氏,宣公16年(-593),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公元年(-590),王師敗于茅戎,成公3年(-588),晉郄克、衛(wèi)孫良夫伐廧咎如,成公6年(-585),伊雒、陸渾、蠻氏之戎與晉伯宗、衛(wèi)孫良夫、鄭人侵宋,成公9年(-582)冬,秦人白狄伐晉,成公12年(-579),晉人敗白狄于交剛,襄公2年(-571)春,齊侯伐萊,襄公5年(-568),王使王叔陳生愬蠻氏之戎于晉,襄公6年(-567)冬,齊侯滅萊,昭公元年(-541),晉荀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昭公元年(-541),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昭公元年(-541)夏,晉荀吳帥師敗白狄于大鹵,昭公4年(-538)夏,楚子、諸侯、淮夷會于申,七月,楚子以諸侯、淮夷伐吳,昭公12年(-530)秋,晉荀吳滅肥,冬,晉伐鮮虞(中山),昭公13年(-529)秋,晉荀吳伐鮮虞(中山),昭公15年(-527)秋,晉荀吳伐鮮虞,圍鼓,昭公22年(-520),晉籍談士蔑帥九州島之戎以納王于王城,昭公22年(-520)六月,晉荀吳再滅鼓,定公3年(-507)秋,鮮虞(中山)人敗晉師于平中,定公4年(-506),晉士鞅、衛(wèi)孔圉帥師伐鮮虞(中山),定公5年(-505)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中山),哀公3年(-492)春,齊衛(wèi)圍戚,求援于中山,哀公6年(-489)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中山)。以經(jīng)傳所記,終春秋之世,戎狄之患,無時或無。齊桓晉文攘夷狄于外,而若揚、拒、泉、皋、伊、洛之戎,為禍近于京師,赤狄、陸渾、蠻氏之戎侵擾輒在左邇。中原諸夏的夷夏界分觀念可以說正是在這樣的擾攘現(xiàn)實中起于對夷狄防不勝防的憂患。這種憂患意識在春秋文獻中有所表露:
1、《左傳·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2、《左傳·莊公31年》:“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3、《左傳·僖公21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
4、《左傳·定公10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正是基于這種憂患意識與變通策略,春秋時期的夷夏觀念并非嚴格區(qū)分的族群觀念,而是往往以是否尊奉天子,從合諸夏為標準。
1、《左傳·僖公15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案:徐本是戎夷,因楚(蠻夷)伐之,而視同諸夏。
2、《左傳·襄公12年》:“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
案:楚大夫子囊議共王謚號,稱楚撫有諸族為蠻夷,而自稱屬諸夏。如此則此一蠻夷,彼一蠻夷,究竟誰是蠻夷,殆未可知也。
3、《谷梁·襄公7年》(經(jīng))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wèi)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案:鄭伯欲會中國諸侯,谷梁子乃稱之為中國之君;鄭大夫欲從楚,谷梁子乃夷狄之。是以夷夏之分,并非以民族或地理為界限,而已變?yōu)橐环N政治文化分野。即如韓愈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63]
所以春秋時期夷夏之觀念似有雙重的標準,一方面由夷狄的侵凌,周室的播遷而產(chǎn)生的憂患意識使周與中原諸夏時時念念“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書·舜典》)春秋經(jīng)傳每欲嚴于夷夏之大防,“《春秋》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公羊傳·成公15年》),《春秋》三《傳》一直宣言“不以夷狄之主中國”(《公羊傳·昭公23年、哀公13年》),“不以夷狄之執(zhí)中國”(《公羊傳·隱公7年》),“不以夷狄之獲中國”(《左傳·昭公10年》),“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谷梁·襄公7年》)。而另一方面,此憂患意識在面對背主棄盟、滅國絕祀者相繼的擾攘現(xiàn)實時,不得不取一種變通之態(tài)度。吳雖夷狄,“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則吳進矣”(《谷梁·定公4年》)。若其尊號令,奉壇盟,則夷狄猶中國也,若其僭尊位,背夏盟,則中國亦新夷狄也。這種包容性和變通態(tài)度,追其思想根源,應與西周至東周這一發(fā)生歷史劇變時期,周人的夏的觀念的演變有很大的關系。平王東遷以后,夏已由比較單純狹隘的地理民族概念,演變?yōu)榘葜袊T姓的一個比較寛泛的政治概念。
綜上所述,夏(中國)與夷之分在西周和春秋時期有如下不同的標準:
一、以地理分:《國語》所紀祭公謀父對穆王說:“夫先王之制,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64]是西周之世,蠻夷戎狄的概念本亦由地理遠近,職貢高低而分。《周禮·夏官》分天下為九服:“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wèi)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zhèn)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65]《書·康誥》有所謂五服,為侯、甸、男、采、衛(wèi)。[66]《書·酒誥》云為侯、甸、男、衛(wèi)、邦伯。[67]“召誥”云“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又無衛(wèi)。《書·益稷》《書·禹貢》則紀其名為:侯、甸、綏、要、荒。[68]此類諸侯職貢名稱,商代已有,[69] 而蠻夷戎狄之列于要荒,似是自西周時期始有的觀念。西周初的文獻《尚書》諸誥中尚無此觀念。《書·旅獒》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故蠻夷作為地理概念,西周時期已經(jīng)顯著,春秋時期亦延用此觀念。孔子欲居「九夷」,又云蠻貊之邦可行也。
二、以民族分:夷夏觀念本是兩種不同血緣民族的區(qū)分,自不待言。《左傳·成公八年》載季文子“《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春秋時期不僅視夷狄為異族,并且以異類視之。周襄王欲納狄女為后,大夫富辰說:“狄,封豕豺狼也。”(《國語·周語》)管仲對齊桓公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左傳·閔公4年》)夷狄之名曰蠻、夷、閩、貉、戎、狄、曰獫(玁)狁、曰獯鬻,是皆以豺狼蟲豸視之。周定王對士季說:“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洽,若禽獸焉。”[70]
三、以文化禮俗分:春秋之世,或視夷狄為異類,此既是就種族之不同而言,亦就禮俗而言。《左傳·襄公9年》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秦穆公問由余:“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71]在中國之人中,以禮樂法度之勝于夷狄是一種比較普遍的觀念。故春秋中國之人對蠻夷戎狄的態(tài)度,有所謂“以德綏戎”(魏絳),“修文德以來之”(孔子)之法。[72]
四、以政治分:則以是否尊奉周天子,是否從合夏盟為標準,來判定夷夏之別,春秋經(jīng)傳往往以此論進退,別華夷,已見前論。
本文認為春秋時期這種以不同標準,多層面判別夷夏的觀念,并非旦夕而成,它實際上包涵了深刻的歷史內(nèi)涵,也蘊含了不同時期周人的不同民族觀念。而夷夏之分的這種多層次、多標準的特性,對我中國的影響,至為深遠。純粹以文化禮俗和政治來分別夷夏,體現(xiàn)了周人的一種包容性和變通態(tài)度。而在歷史上夷夏紛爭尖銳到無法調(diào)和時,它往往能起到一定的稀釋作用。《宋書?五行志》卷31:“晉武帝太康后,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shù)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后。’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73]是魏晉時期猶以“中國”指據(jù)有中原之晉,而與吳并舉。而《宋書?柳元景傳》卷77:“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nèi)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并為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后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zhàn)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74]此“中國”蓋指南朝之宋。《宋書?索虜列傳》卷95:“(宋)太祖踐祚,便有志北略。七年三月,詔曰:“河南,中國多故,湮沒非所,遺黎荼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jīng)理,以固疆埸。”[75] 劉裕所說的中國指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地區(qū)。從上例可以看到,南朝時期的中國觀念,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民族、政治名詞。對于南朝宋人來說,晉是中國,此就中原的正統(tǒng)而言,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北朝魏治下的中原也是中國,此就地理概念而言;偏安江左的南朝宋也是中國,此就其政治上的正統(tǒng)性而言。似此概念之優(yōu)容,準的之未一,適為后世師夷變夷、折沖尊俎,提供一轉圜地。中國歷史上的夷夏觀念,也如中國概念一樣,每每因時、因地、因人不同而有轉圜的余地。金元時期,一些漢族和漢化的其它民族的知識分子都從文化、禮俗的角度來界定“中國”“華夏”的觀念,從而置換“中國”“華夏”的地理概念和民族內(nèi)涵,藉以在政治上為異族入主的正統(tǒng)性尋求理論依據(jù)。[76] 清初學者,于夷夏之辨不可謂不嚴,顧寧人(顧炎武)所謂“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77]呂晚村(呂留良)所謂:“華夷之分,大過于君臣之倫,”[78]王船山(王夫之)所謂“天下之大防,人禽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tǒng),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于戴異類以為中國主。”[79]此其皆就本民族的利益而言,清初學者于血緣亦十分重視,一本諸春秋時期“戎狄豺狼,諸夏親昵”之觀念。然而,雍正針對的觀念是:以正統(tǒng)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以地理論,“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以種族論,指出“夷夏一家”,并追溯其先世為黃帝之后;以文化論,自清初開國尊孔開科等,皆從中國禮俗,“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80]從這幾個方面出發(fā),雍正可說在理論上解決了漢族知識分子的夷夏觀問題。故夷夏之別,由夷夏之辨本身的多重性和包容性而消匿于無形。以此看來,春秋辨華夷之義,嚴夷夏之防適為后世用夏變夷、及師夷之長技張本。
注釋:
[1]王鐘翰主編:《中國民族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71。
[2]錢穆:《國史大綱》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
[3]《國史大綱》頁12。章太炎以為,”今直隸淮南皆謂山東人為‘侉子’,侉即華之聲借,若華亦作荂矣。”見“新方言”二,《章氏叢書》杭州:浙江書局刊本,1918年,第1函,第7冊,頁39上。此又別為一解。
[4]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年,頁1093-1134。
[5]據(jù)文獻所載,杞繒歷商而再封于周初武王時期。杞于公元前五世紀中期為楚所滅,繒于公元前567年為莒所滅。見陳盤《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2:121b-126a;4:298a-305b。春秋后期至為強盛的越國,傳亦為夏少康之后。《史記?越世家》:“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
[6]“華夏”一詞,春秋以前文字中僅一見。《尚書?武成》云:“今商王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傳》曰:“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孔《疏》:“冕服采章對被髪左衽,則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見《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頁185。余按:此“華夏”非謂中國也。是篇前文有:“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勛,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傳》注“方夏”云:“以撫綏四方中夏。”余按:方夏者,夏方也。其用法一猶“區(qū)夏”(“康誥”)。華夏猶言有冕服采章之美之夏方也。故華夏所指仍是周邦,其實亦周人自我夸飾之語。此說征之金文字形,允信。金文華作“一蒂五瓣之形”(林義光《文源》),為花之初文。故以花之絢麗形容文章黼黻之美。如此則華夏之華,初非地名。
[7]陳夢家:《卜辭綜述》,頁291-2。
[8]Cho-yun Hsu and Katheryn Linduff,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8),41-2.
[9]Elman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NewYork: RandomHouse, 1962).
[10]張光直:“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系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中國青銅時代》,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1994年,頁31-63;“殷周關系的探討”《中國青銅時代》頁91-119。
[11]許倬云:《西周史》頁63。
[12]《尚書通論》,頁112。
[13]《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頁224。
[14]《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頁203。
[15]“長夏”見《大雅?皇矣》;“時夏”見《周頌?時邁》、《周頌?思文》;“時周”《周頌?賚》、《周頌?般》。朱《詩三百篇探故》,頁66-67。
[16] 楊伯駿:《春秋左傳注》頁1307-1308。
[17]《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頁231。
[18]《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頁212。
[19]《尚書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頁213。
[20] 王克林:“略論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關問題”《夏史論叢》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頁79-80。
42Acculturation 人類學界一般譯作“涵化”。
[22]見拙文“說夏與雅:宗周禮樂形成與變遷的民族音樂學考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2001年9月):頁46-47。
[23]許倬云:《西周史》頁119-20。Hsu and Linduff, 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123.
[24]《周禮注疏》見《十三經(jīng)注疏》頁892。
[25]《書·酒誥》:“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wèi)、邦伯;越在內(nèi)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酒誥”一篇周人亦皆以西土自居,而稱中原之地曰“殷國”。
[26]《尚書正義》,頁202-3。
[27]于省吾引何尊銘文以為“中國”一詞,武王時期已出現(xiàn)。見“釋中國”《20世紀中華學術經(jīng)典文庫?歷史學?中國古代史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4-180。
[28]見胡厚宣:“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的起源”,《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海:上海書店,1944年,頁383-388。
[29]姚孝燧主編蕭丁副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頁778。
[30]田倩君:““中國”與“華夏”稱謂之尋原”《大陸雜志》,第31卷第1期,頁19。
[31]章太炎:“中華民國解”《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一”,見《章氏叢書》杭州:浙江書局刊本,1918年,函3,冊26。
[32]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82年,頁442-3。
[33]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職官系統(tǒng)”,收入?yún)菢s曾編:《盡心集:張振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210-1。
[34]見敔簋、曾伯旅叵、翏生盨、駒父旅盨、彔 尊、兮甲盤、禹鼎及其它銅器銘文。
[35]見無簋、史密簋、宗周鐘、競卣及其它銅器銘文。
[36]宗周鐘、小臣言逨簋、禹鼎等。
[37]史密簋。
[38]師酉簋、詢簋銘文。
[39]師酉簋、詢簋銘文。
[40]師酉簋、詢簋銘文。
[41]師酉簋、詢簋銘文。
[42]師酉簋。
[43]能原鐘與能原镈。
[44]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9.21.2-9.24.1。
[45]尚志儒:“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夷問題”《西周史論文集》頁231-2。
[46]唐蘭:“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考釋”《考古學報》4[1]:24-25,及“何尊銘文解釋”《文物》1976年第1期,頁63。
[47]見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73。
[48]白川靜釋靜簋銘中服為職官名,釋詢簋銘中服為一種軍士(參見《金文通釋》16.84.127;31:182.705).以兩器銘文參照來看,服之服似為一種軍士充任宮廷護衛(wèi)之職,“服夷”指出這些軍士的族群來源。
[49]井侯簋又名榮作周公簋,為西周早期器,見《殷周金文集成》,8.4241。
[50]中方鼎為西周早期器,見《殷周金文集成》,5.2785。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92。
[51]宜侯?簋、曶鼎。
[52]《睡虎地秦墓竹簡》頁206。
[53]《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戰(zhàn)國從橫家書》“蘇秦謂齊王章”(一)《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冊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頁61。
[54]《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808。
[55]《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744。
[56]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607。
[57]《重刊宋本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重印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頁16。
[58]見拙文“說夏與雅:宗周禮樂形成與變遷的民族音樂學考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2001年9月):頁39。
[59]許倬云:《歷史分光鏡》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170-1。
[60]Herrlee G. Creel, Origins of the Statecraf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197.
[61]本文初發(fā)表于1999年6月18日在臺北圓山飯店舉辦的《中華民族邁向21世紀學術研討會》。會間,王仲孚教授曾提出意見,指出徐復觀先生認為周人的 “憂患意識”西周初年已有。我認為周初之憂患意識與春秋時期的憂患有所不同。當然憂患意識周初的周人已有,多見于《尚書》諸誥中。而周初周人的憂患,來自于對不可知的天命的敬栗,而平王東遷以后周人的憂患,則更多地是對“王室將卑,戎狄必昌。”的憂慮。
[62]顧棟高:“春秋四裔表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159-2161。
[63]韓愈:“原道”《韓昌黎文集》(《四部備要》本),卷11,頁4。
[64]《國語》,卷1,頁4。
[65]《周禮注疏》,卷29,頁197,見《十三經(jīng)注疏》,頁835。
[66]《尚書正義》,卷14,頁95,見《十三經(jīng)注疏》,頁207。
[67]《尚書正義》,卷14,頁95,見《十三經(jīng)注疏》,頁207。
[68]《尚書正義》,卷5,頁31;見《十三經(jīng)注疏》,頁143。《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wèi);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見《尚書正義》,卷6,頁41,《十三經(jīng)注疏》,頁153。
[69]見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wèi)’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wèi)’等幾種諸侯的起源”,《古代文史研究新探》,頁343-365。
[70]《國語》,卷2,頁62。
[71]《史記》,卷5,頁192。
[72]見姜建設:“夷夏之辨發(fā)生問題的歷史考察”,《史學月刊》1998年第5期,頁18。
[73]《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31,頁914。
[74]《宋書》,卷77,頁1985。
[75]《宋書》,卷95,頁2331。
[76]關于金元時期漢族與漢化的其它民族知識分子,如元好問、趙秉文、郝經(jīng)、楊維禎等人的“中國”觀,可參見何志虎““中國觀”在元代的轉換”一文,見《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5期(2002年10月):頁53-56。
[77] 見黃汝成集釋,顧炎武撰:《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7,〈管仲不死子糾〉條,頁11下。
[78] 呂說見《大義覺迷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卷2,“奉旨訊問曾靜口供二十四條”曾靜供述,頁11上。
[79]王夫之:《讀通鑒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3,頁416。
[80] 見郭成康:“也談滿族漢化”《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頁29引自《清世宗實錄》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