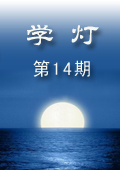
《學燈》2010年第2期(總第14期)
主 編:李銳 朱清華
周 期:季刊
出版時間:2010年4月
述《五禮通考》之成書
張濤(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清味經(jīng)秦蕙田纂修《五禮通考》一書,以《周官》五禮分目,匯古今諸儒聚訟之說,附以歷朝史志,為之疏通駁解,使后之考禮者一編在手,如覽眾書,而列代沿革,亦備于目前,其有功經(jīng)義,良不鮮也。
今不自揆,就其成書史事略加稽考,先述其纂修始末以為經(jīng),再敘與事二十余人之情況,以為緯,兼及該書版本源流與各本得失,聊供世之讀是書者參酌討論。深愧所見不廣,所得未深,倉促成文,殊難賅備,查疑補缺,俟諸異日。
一、《五禮通考》纂修系年
雍正二年甲辰(1724),秦蕙田二十三歲,與同邑友人相約讀經(jīng),期月二會,前后十有余年。諸君參錯禮書,往復問難,隨讀隨記,積藁百卷。
《五禮通考》卷端秦氏《自序》云:“甲辰,年甫逾冠,偕同邑蔡學正宸錫、吳主事大年、學士尊彛兄弟為讀經(jīng)之會。”
案蔡德晉,字宸錫。吳鼐,字大年。吳鼎,字尊彛。
秦氏《自序》又云:“相與謂三《禮》自秦漢諸儒抱殘守闕,注疏雜入?緯,轇輵紛紜。……乃于禮經(jīng)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先之以經(jīng)文之互見、錯出足相印證者,繼之以注疏、諸儒之抵牾訾議者,又益以唐宋以來専門名家之考論發(fā)明者。每一事一義輒集百氏之說而諦審之,審之久思之深,往往如入山得徑,榛蕪豁然;又如掘井逢源,溢然自出。然猶未敢自信也。半月一會,問者、難者、辨者、答者回旋反復,務(wù)期愜諸已、信諸人而后乃筆之箋釋,存之考辨。如是者十有余年,而裒然漸有成帙矣。”
案秦《序》追憶讀經(jīng)之會緣起、諸君論難情實頗為生動詳盡,良可寶貴,雖不若后撰《凡例》之該備,然大綱草創(chuàng),亦具體而微者也。觀此可以見古人著作發(fā)端、賡續(xù)之艱難,所謂先河后海之意。此序作于乾隆二十六年。另秦氏友人諸氏洛,乾隆十九年撰《書〈味經(jīng)窩圖〉后》,內(nèi)述讀經(jīng)之事,可與此互參,姑錄數(shù)語如次:“與同里蔡學正敬齋、吳工部容齋、學士易堂,龔布衣繩中聯(lián)解經(jīng)會。朔望必集,各出疑義相質(zhì),如是者數(shù)年,成經(jīng)說百余卷。”內(nèi)龔粲字繩中,為秦《序》所遺。
又案自本年始,為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一期。
雍正三年乙巳(1725)。春,諸人詳考禮書“袒裼襲”之義。未幾,蔡德晉成《袒裼襲記》與《袒裼襲解辨》二文。
《五禮通考》卷二百二十賓禮“天子諸侯朝”門:“蕙田案:禮文有經(jīng)傳明據(jù)而淆于諸儒之岐說者,莫如袒裼襲之義。少時與同學諸子病之。雍正乙巳春,遂相與徧考經(jīng)文,詳稽眾說,久乃豁然融貫,迎刃而解。搜集則吳氏鼎之力居多,此二說則蔡氏筆也。棼絲就理,翳障頓開,凡三閱月而后定。嗚呼,讀經(jīng)豈易焉!”
案所云“此二說”,指蔡氏德晉《袒裼襲記》及《袒裼襲解辨》,俱見《五禮通考》本卷,后嚴杰輯《經(jīng)義叢鈔》,卷十二亦錄此二文,唯前者名《袒裼襲說》。
乾隆十年乙丑(1745)。秦氏遷禮部右侍郎,承命校閱禮書,于五禮沿流,詳加考究。
《清史列傳·大臣畫一傳檔正編十七·秦蕙田》:“十年,遷禮部右侍郎。”
《五禮通考自序》:“乙丑簡佐秩宗,奉命校閱禮書。”
案前此乾隆元年丙辰(1736),秦氏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南書房行走,見《清史稿》卷三〇四本傳。其間修書一事,不曾或輟,本《序》所謂“丙辰通籍,供奉內(nèi)廷。見聞所及,時加厘正”者是。至佐貳禮部,得閱禮書,于纂修《五禮》之舉幫助良多,故本《序》自道其事云:“時方纂修《會典》,天子以圣人之徳,制作禮樂,百度聿新。蕙田職業(yè)攸司,源流沿革不敢不益深考究。”
秦蕙田《周易孔義序》:“蕙田登第,由翰林貳秩宗,方從事《五禮》。”
案秦氏自稱“《五禮》”,此為初見。
又案自秦氏及第入京為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二期,其間數(shù)事,影響《五禮通考》纂修甚巨,晉升秩宗,乃其一也。
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五月,以本生父秦道然身故,丁憂在家,仿徐干學《讀禮通考》,復加更張,訂制《五禮通考》綱目規(guī)模。
《清史列傳·秦蕙田》:“十二年五月,丁本生父憂。”
《五禮通考自序》:“丁卯、戊辰治喪在籍,杜門讀禮,見昆山徐健庵先生《通考》。”
案雍正間諸君排比經(jīng)注、眾說,匯為一編,然未嘗以《五禮》名之。至第二期,始見《五禮》之稱。據(jù)本《序》,秦氏以徐干學《讀禮通考》“規(guī)模義例具得朱子本意,惟吉嘉賓軍四禮尚屬闕如”,遂“一依徐氏之本,并取向所考定者,分類排輯,補所未及”,與本書《凡例》所謂“五禮之名,肇自《虞書》,五禮之目,著于《周官·大宗伯》,曰吉兇軍賓嘉,《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至近代昆山徐氏干學著《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古禮則仿《經(jīng)傳通解》,兼采眾說詳加折衷;歴代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通考》,廣為搜集,庶幾朱子遺意所闗,經(jīng)國善俗,厥功甚巨,惜乎吉、嘉、賓、軍四禮屬草未就。是書因其體例,依《通典》五禮次第編輯,吉禮如干卷、嘉禮如干卷、賓禮如干卷、軍禮及兇禮之未備者如干卷,而《通解》內(nèi)之王朝禮,別為條目,附于嘉禮,合徐書而大宗伯之五禮古今沿革、本末源流、異同失得之故,咸有考焉”正合,可知《五禮通考》全書條目,至此略定。
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四月,秦氏將服闋,仍起禮部侍郎。此后,方觀承、盧見曾、宋宗元均許同訂《五禮通考》。
《清史列傳·秦蕙田》:“十三年四月,奉旨:‘秦蕙田服制將滿,著仍以禮部侍郎調(diào)用。’”
《五禮通考自序》:“服闋后再任容臺,徧覽典章,日以增廣。適同學桐山宜田領(lǐng)軍見而好之,且許同訂。宜田受其世父望溪先生家學,夙精三禮,郵籖往來,多所啟發(fā),并促早為卒業(yè),施之剞氏,以諗同志。德水盧君抱孫、元和宋君愨庭從而和之。”
案宜田、方觀承字,抱孫、盧見曾字,愨庭、宋宗元字是也。
又案據(jù)《清史列傳》本傳,本年三月,方觀承擢浙江巡撫,十四年末擢直隸總督,兼理河道。則方氏應(yīng)允同訂《五禮通考》事,當在明年末返京任職之后。盧見曾為《五禮通考》作序,參下乾隆二十年條。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五禮通考》初稿垂成,顧棟高入都,正月十六日,為作序言。
《五禮通考》卷端顧棟高《序》:“少宗伯秦公味經(jīng)輯《五禮通考》一書,凡若干卷,書垂成而余入京師,屬為之敘。……乾隆十七年壬申顧棟高時年七十有四。”
案據(jù)顧氏《萬卷樓文稿》,此序作于本年正月中浣六日。秦氏時方任職刑部,文中稱“少宗伯”者,據(jù)舊銜也。所謂“書垂成”者,見下年案語。顧又嘗與秦氏《五禮通考》論纂修事,多所攻錯,詳本稿二節(jié)。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八月,蔣汾功序《五禮通考》。吳玉搢主秦宅,訂《五禮通考》。秦蕙田陪祀,與人論明堂之制。
《五禮通考》卷首蔣汾功《序》:“今秋兒子和寧給假歸里,爰以授之,而索予弁其首。予讀之,聽然莫逆于心也夫。……故不敢以老辭,序而歸之。乾隆十有八年秋八月陽湖八十二老人蔣汾功。”
案自乾隆元年秦蕙田登第進京,至十七、八年間顧棟高、蔣汾功各為撰序,為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二期。其時秦氏依據(jù)舊稿,勤加增益,小成初稿,顧《序》所謂“書垂成”者,指此而言。蔣《序》謂秦氏“早歲即洞其條理,綜核纂注,彚為一編”,是為舊稿;“通籍后簪筆承明,毎稍暇輒抒思厘定,至晉居秩宗而帙始成,”則此初稿是也。《五禮通考》一書,纂修歷時甚久,其大綱大目雖麤具于乾隆丁卯、戊辰間秦氏丁憂之際,然至顧、蔣二人作序時,仍不言其書卷數(shù),故知此初稿尚有疏漏,難稱詳備,非今所見《五禮通考》之比也。前人有以今見《五禮通考》為“乾隆十八年本”者,殆未是,說詳本稿第三節(jié)。
段朝端《吳山夫先生年譜》“乾隆十八年癸酉五十六歲”條云:“蓋先生于是年由歲貢入都試教席,主秦樹峰司寇家。”
案段氏引吳玉搢《〈亭林集〉跋》“亭林先生全集,予得于雍正改元之十一月,……越二十余年北游燕冀”云云。夫本年去雍正元年三十余載,與吳云“二十余年”不侔,不當以吳氏本年始入都,故段《譜》“二十三年戊寅”條下小注又云“或壬申(引者案乾隆十七年)已入都未可知”。要之,吳玉搢前此已至京師,唯本年始館于秦宅耳。丁晏所撰年譜謂明年吳氏入都,非。
《五禮通考》卷廿四:“又案上圓即九室,下方即十二堂。或疑其制難于營建。乾隆癸酉,予適陪祀,見少司空長白三公名和。三精于營造,予問曰:‘考古明堂之制,應(yīng)如是,可乎?’曰:‘可。’并言今大高殿后有一殿,上圓下方,明嘉靖時所建也。古法有之,論乃定。”
案觀此可知秦氏為學,不廢實踐,非祇書本上面討生活也。其古今比核之法,亦通貫《五禮通考》全書。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初,《五禮通考》積稿二百余卷,復邀錢大昕助纂。戴震由錢大昕之介,得識秦氏,為講天算推步,并紹介江永之歷學。王鳴盛、王昶亦與其事。
諸洛《書〈味經(jīng)窩圖〉后》云:“著《五禮通考》二百余卷,補徤庵徐公《讀禮通考》之闕。庚午,改刑部侍郎,于今五年。……甲戌元日,公招飲,止宿邸第,手此圖屬書語。”
案諸洛此文作于本年元日,內(nèi)云“《五禮通考》二百余卷”,因知該書至此規(guī)模大備,猶在錢、戴諸人襄助以前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傳》:“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師,困于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目為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wù)摼谷铡ィ枘克椭瑖@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于推步者。予輙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卽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為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采其說焉。”
案《竹汀居士年譜》本年條稱“無錫秦文恭公邀予商定《五禮通考》。休寧戴東原初入都,造居士寓。談竟日,嘆其學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與居士同車出,親訪之”云云,可與參看。戴震入都之年,王昶《春融堂集·戴東原先生墓志銘》、凌廷堪《校禮堂集》卷三十五《戴東原先生事略狀》并同《竹汀居士年譜》。段玉裁撰《戴譜》誤作乾隆二十年,茲從錢賓四先生辨正,系于本年。段君《戴東原先生年譜》引紀昀《考工記圖序》曰:“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金匱秦文恭公聞其善步算,即日命駕,延主其邸,朝夕講論《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門,以為聞所未聞也。”則秦氏招戴震講論,經(jīng)年未輟也。今《五禮通考》內(nèi)戴震按語往往而有,而“觀象授時”一門所載尤伙。段君又言“文恭全載(戴)先生《句股割圜記》三篇,為古今算法大全之范”,實則《五禮通考》收錄戴氏此文,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后,故味經(jīng)窩通行本《五禮通考》有之,而味經(jīng)窩初刻試印本尚付之闕如也,詳本稿第三節(jié)。
又案自本年始,為纂修之第三期。
《戴東原集》卷十二《江愼修先生事略狀(壬午)》:“其后,戴震嘗入都。秦尙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shù)篇,奇其書。戴震因為言先生。尙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jīng)綱目》也。”
案江永《推步法解》見《五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至卷一百九十七。
又案戴君此文作于乾隆二十七年,故以“尚書”稱秦氏。實則秦氏擢領(lǐng)工部、兼署刑部尚書在乾隆二十二年,本年尚為侍郎。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五《王鳴盛傳》:“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受編修,公卿爭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于掌院學士蔣溥。”
嚴榮《述庵先生年譜》本年條云:“正月北上,二月抵京師,禮部侍郎無錫秦公(蕙田)方仿徐氏《讀禮通考》之例纂《五禮通考》,屬先生修吉禮。”
案據(jù)此則秦氏延聘諸人當在二月后。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冬,秦蕙田以《五禮通考》全書示盧見曾,囑其作序。
《五禮通考》卷端盧見曾序:“乙亥冬,今秦大司寇味經(jīng)秦先生辱示《五禮通考》,……書成,征序于余”云云。
案秦氏諸人纂修《五禮通考》,孜孜不倦,時獲新境,此言“書成”,云成而實未成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錢大昕館于秦宅, 參校《五禮通考》。
《潛研堂文集》卷廿六《味經(jīng)窩類稿序》:“丁丑、戊寅之間,館公邸第,因得稍窺公得力所自。”
秦氏《自序》:“戊寅,移長司寇,兼攝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錢宮允曉征實襄參校之役。”
案秦氏自敘其事,屬之明年。然據(jù)《清史列傳》秦氏本傳,調(diào)任刑部尚書,兼管工部,事在二十三年正月。前此錢大昕或已至秦邸,所謂“丁丑、戊寅之間”,固得其實。秦《序》于助纂眾人,除同邑友好并諸顯宦外,唯及錢氏,則謂錢氏之于《五禮通考》纂修一事,居功至偉,自非過當。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冬,《五禮通考》成,秦蕙田作《自序》。
秦氏《自序》:“辛巳冬,爰始竣事,凡為門類七十有五為卷二百六十有二。自甲辰至是,閱寒暑三十有八,而年亦已六十矣。”
案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三期,至本年止。味經(jīng)窩初刻試印本之刊印,當在本年前后,詳本稿第三節(jié)。如上條陳,凡此三十八年之間,歷經(jīng)三期:雍正二年至雍正十三年為第一期,秦蕙田與鄉(xiāng)人為讀經(jīng)之會,積稿成帙,都百余卷;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為第二期,秦氏登第入京、任職禮部、讀校禮書、及丁憂回籍數(shù)事,于《五禮通考》之纂修,影響莫大焉,而成稿亦逾二百卷;乾隆十九年至本年止,為第三期,秦氏得錢、戴眾新進才雋之助,續(xù)加葺補,終期大備。自雍正二年起,前后幾四十年,秦氏孜孜經(jīng)營,今始垂成。此中甘苦,略可想見,而經(jīng)始諸人如蔡德晉、吳鼐,均已徂謝,他若顧棟高輩,亦不及見此書之成。
又案自此以后,即纂修《五禮通考》之修訂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二月廿日,盧文弨為跋《五禮通考》。
盧文弨《五禮通考跋(癸未)》:“吾師味經(jīng)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硏,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古今之菁英盡萃于此矣,洵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案或本《五禮通考》書前所附跋文與盧《集》字句稍異,末云“歲在癸未二月既望五日,受業(yè)盧文弨拜識”。
又案據(jù)《竹汀居士年譜》、《戴東原年譜》等書,本年秦蕙田奉詔修《音韻述微》,錢、戴二人嘗預(yù)其事。此編纂《五禮通考》將成,乃有余力為之也。此事今不俱論,唯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銘》謂秦氏奏江永韻學湛深,“詔取《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進承,以備采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于《五禮通考》”,似《推步法解》始載于《五禮通考》者。然二十六年所刊《通考》已將慎修此文收錄,王君之《銘》但以事類相近,牽連行文,未可以編年實錄視之。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盧文弨致書秦蕙田,言《五禮通考》“可參酌者”十五事。九月九日巳時,秦氏卒于滄州,十一月謚文恭。
《抱經(jīng)堂文集》卷十八《復秦味經(jīng)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甲申)》云:“日承尊諭,以所著《五禮通考》雖已刊刻完竣,未即行世,恐其中或有參錯不及細檢處,須及今改訂為善。……謹就愚見,似其中尙有可參酌者數(shù)事,輒疏左方呈覽,伏乞恕其狂瞽。或有一二采擇,不勝幸甚。主臣。”
案盧氏此文為二十六年本《五禮通考》糾謬,其所云“可參酌者”十五事,為通行本《五禮通考》采用者五、未用者七、酌情采用未能盡改者三。可知今通行本《五禮通考》之勘定,必在本年以后,詳見拙文《味經(jīng)窩本〈五禮通考〉刊刻年代考》。因本年九月秦氏驟然下世,此通行本之修訂暨盧氏糾謬之去取,是否秦氏手定,尚難確定。
《清史列傳·秦蕙田》:“二十九年,充經(jīng)筵講官。……四月,以病請解任,諭曰:‘秦蕙田,不必解任,題奏事件照常辦,尋常咨行事,暫且不必畫稿,俾得從容調(diào)攝。’八月,復請解任回籍,諭曰:‘秦蕙田以現(xiàn)在病尚未痊,奏請開缺,給假回籍就醫(yī)。著照所請,準其給假南旋,即可乘便就醫(yī),而江鄉(xiāng)水土于伊調(diào)攝自必相宜,可以日漸痊愈。刑部尚書不必開缺,其事務(wù)著劉綸兼署。’九月,卒于途。……尋賜祭葬如例,謚文恭。”
《光祿大夫經(jīng)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尙書秦文恭公墓志銘》:“以九月九日巳時薨于滄州。”
《清通志》卷五十二:“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秦蕙田,謚文恭。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謚。”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高宗下詔征書。其后,江蘇省以此書進呈。
《江蘇采輯遺書目錄》:“《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刊本)。”
案此刊本當即味經(jīng)窩之修訂通行本。
二、《五禮通考》與事學人名錄
上節(jié)檢選所見系年資料匯為一編,歷述《五禮通考》成書始末,雖尚簡陋,然條目粗具,可備參酌。惟參編《五禮通考》之人,有頗乏具體年月可考者,乃無由增入,甚為可惜。茲作“《五禮通考》與事學人名錄”一節(jié),相為經(jīng)緯,則《五禮通考》之纂修情實,或因此而益彰。
昔王大隆欣夫先生跋所藏稿本《五禮通考》,謂秦氏“少時與同里顧棟高、吳鼎、龔燦、吳鼐、蔡德晉諸人為讀經(jīng)會,于《禮》考訂辯正,必求其是,筆錄存之,成經(jīng)說百余卷。及官禮部侍郎,即據(jù)此及蔡德晉書為藍本,撰《五禮通考》以廣徐干學《讀禮通考》之未及。博諮當時通儒,助之成書者,有金匱吳鼎、德州盧見曾、嘉定錢大昕、王鳴盛、休寧戴震、仁和沈廷芳、吳江顧我鈞”,又謂“青浦王昶亦預(yù)參校,而卷中未分注名氏”,“方觀承、宋宗元后來出資付刻,故每卷并列其名,而兩家案語悉出后增”。此語大略得其仿佛,第不無小誤,且猶有未盡。
夫是書之纂修,發(fā)端于錫山讀經(jīng)會。當時除秦蕙田而外,尚有蔡德晉、吳鼐、吳鼎,
《五禮通考》卷端秦氏《自序》,見上節(jié)“雍正二年甲辰”條。
又有龔燦。
《清儒學案》卷六十七《味經(jīng)學案》載《味經(jīng)日鈔自序》云:“余少與蔡學正宸錫、吳水部大年、學士尊彝、龔布衣繩中為讀經(jīng)之會。”較《五禮通考自序》多龔繩中一人,即王欣夫所說“龔燦”,諸洛《書味經(jīng)窩圖后》、錢大昕《光祿大夫經(jīng)筵講官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秦文恭墓志銘》所記皆有此人。
內(nèi)中蔡德晉氏,貢獻尤多,惜乎大著未就,先行下世。
王大隆謂《五禮通考》據(jù)蔡氏書為藍本。案王昶《蒲褐山房詩話》 “蔡德晉”條云:“宸錫先生精通三禮,嘗分門別類,以次相從,采掇鉤貫,凡五十余冊,功未竟而歿。秦文恭公少與同學,得其本而增修之,證以歷朝史事,補以宋、元諸儒之說。今所傳《五禮通考》,雖續(xù)健庵尚書《讀禮通考》之遺,實則據(jù)先生書為藍本。今其書割裂之余,無有存者。”此即王說所本。然當日諸人讀經(jīng)問難、筆錄成篇非必一二人之功,觀上節(jié)“雍正三年乙巳”條可見。且秦氏自有積稿,蔡氏之說亦后來增益也,如稿本《五禮通考》卷六一頁廿一、卷二三四頁十三所載蔡說即如此。又《清史稿》蔡氏本《傳》謂其“著《禮經(jīng)本義》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卷,《通禮》五十卷。”《無錫金匱縣志》卷三十九《藝文·著述》則云“蔡德晉,《禮經(jīng)本義》三十九卷(《周禮》二十二卷,《儀禮》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卷、《通禮》八十一卷、《詩經(jīng)集義》十六卷”頗有不同,今存僅《禮經(jīng)本義》十七卷、《敬齋禮說》抄本二種。而《五禮通考》內(nèi)錄蔡氏經(jīng)說甚伙,正可補其著作亡逸之缺憾。
洎后秦氏入都,吳鼎亦舉經(jīng)學,仍屬參校之役,今通行本《五禮通考》數(shù)卷卷首署其名。
顧棟高《萬卷樓文稿》冊四《五禮通考序》有“秦子味經(jīng)與其友吳子尊彝輯《五禮通考》一書”云云,與《五禮通考》卷端所載但稱秦氏不同,可知吳鼎之功,原不可掩。
其后參校者又有顧我鈞、
案稿本、通行本參校者皆有其名。顧氏為顧我琦之弟,我琦曾與秦氏同修《江南通志》,我鈞殆是時結(jié)識秦氏也。我鈞身后寥落,文章傳世者鮮,所見僅《顧發(fā)千雜著》一殘本載有經(jīng)說數(shù)篇。幸賴《五禮通考》保存其文,如卷二十《嘉靖分祀論》、《嘉靖議郊配論》及稿本卷十四《父天母地論》之類。
陸登選、
稿本卷六二、六五題云“貢士陸登選參校”,然后來刊本絕不見其名氏,殆未終其事者歟?《江南通志》卷一百十、《福建通志》卷廿七、卷四一、《重修臺灣縣志》卷九有一名“陸登選”者,福建甌寧人,舉人,嘗為官,年齒略長,豈同姓名耶?
褚寅亮、
稿本卷一百二至一百四、一百六至一百八、一一六至一二二署“中書舍人長洲褚寅亮參校”,通行本則更換他人,未審其故。褚氏與錢大昕、王鳴盛相友善,固精于禮學者,有《儀禮管見》行世。
盛世佐。
馮浩《儀禮集編小引》云:“君(引者案即盛世佐)將赴部時,大司寇錫山味經(jīng)秦公著《五禮通考》,以參校之責屬余,余敬謝不敏,言君于秦公。君乍至,公急以禮館君邸宿,退食之暇,相與論難,或讙然喜,或怫然爭。余每規(guī)君毋憨,而君以經(jīng)術(shù)所關(guān),一字不假借。《五禮通考》中君所論定實居其半,而君自有專書,以為可獨傳也。”此承喬秀巖師惠示。另,盧文弨《書校本〈儀禮〉后》,《〈儀禮注疏詳校〉自序》亦記其事。盛氏乾隆二十年以公事卒江南舟次,其館于秦宅當稍前于此,或與錢大昕諸人相后先也。乃秦氏于盛世佐絕未提及,豈馮氏所說“怫然爭”之故歟?馮氏所云“君所論定實居其半”,固難坐實,然《五禮通考》多有因襲盛氏《儀禮集編》處,所據(jù)且為稿本,與盛書后來版本有異。參見拙文《〈五禮通考〉“喪禮門”編纂評析》。
至纂修《五禮通考》之第三階段,秦氏延請參校是書者,有錢大昕、戴震、
參上節(jié)“乾隆十九年甲戌”、“二十二年丁丑”條。
王鳴盛、
王氏與修《五禮通考》多門,后將所編“軍禮門”部分單獨刊行,《周禮軍賦說》實該部分草稿而已。然王氏所編,稍嫌粗略,故今《五禮通考》相應(yīng)部分對之多有修訂。王氏又有《五禮通考序》,見《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四,筆者所見《五禮通考》各本皆不載此序。
沈廷芳、
《五禮通考》卷二四六至二五一為“兇禮”除“喪禮”之外者,稿本、味經(jīng)窩諸本皆署“按察使司按察使仁和沈廷芳”。
王昶,
王氏與修吉禮,然《五禮通考》卷中未分注名氏,王大隆已言及之。案《蒲褐山房詩話》有“文恭嘗招予寓味經(jīng)窩數(shù)月,予病為按脈定方”云云,殆參與時日甚短,故今吉禮部分不數(shù)王昶其人。
參校者又署盧見曾、宋宗元,方觀承則為“同訂”。
參上節(jié)“乾隆十三年戊辰”條。王大隆謂德州盧見曾“助之成書”,“方觀承、宋宗元后來出資付刻,故每卷并列其名,而兩家案語悉出后增”,“悉出他手”,似盧氏與方、宋二人不同。然盧氏《五禮通考序》初不言此,卷中亦無一條案語,其生平撰作多假他人之手,恐徒具名而已。至若方觀承,則為方苞之侄,《五禮通考》卷首載其序乃言“昔在京師時,伯父望溪先生奉詔纂修三《禮》,余數(shù)從講問”,殆淵源有自,與盧、宋有異。王氏謂其“案語悉出后增”,誠然,《五禮通考》稿本卷一八一署戴震參校,而篇中方氏“案天大”一條,實為別紙新增,卷一八三又有方氏評戴之語可知方氏雖于乾隆十四年許為同訂,其案語則有寫于乾隆十九年后者;而云“悉出他手”,則難以遽定。秦氏此書亦有據(jù)方案而刪改者,見稿本卷二三四頁六、通行本卷二三三頁十、頁卅二、卷二三四頁五等等。《五禮通考》每卷卷首署“方觀承同訂”,異乎彼輩,非偶然也。方氏能吏,又精治河,故《五禮通考》“體國經(jīng)野”一門所載方案尤多。
其參與校字之役者,則尹嘉銓、吳玉搢。
案吳玉搢見上節(jié)“乾隆十八年癸酉”條。《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十九皆吳氏所校。阮葵生《茶余客話》卷二一“吳玉搢《山陽耆舊詩》”條云:“吳山夫?qū)W有本原,館秦樹峰司寇家,《五禮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峰嘗言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此即王欣夫言“統(tǒng)校全書,則屬諸山陽吳氏玉搢(引者案原作縉)焉”之所本。秦蕙田《答顧復初司業(yè)論〈五禮通考〉書》所謂“今所托校讎者,惟淮陰吳山夫一人”,不過言當時情狀,不得云數(shù)十年間數(shù)百卷書皆吳氏一人手訂。今全書卷首四卷、卷卅二至卅六末署“博野尹嘉銓校字”可證。
又案《五禮通考》稿本卷卅八署“吳玉搢參校”,則吳氏不僅校字而已矣。
盧文弨亦曾參酌校訂,
參上節(jié)“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條。案盧氏一則云“吾師味經(jīng)先生因徐氏《讀禮通考》之例而徧考五禮之沿革,博取精硏,凡用功三十八年而書乃成,文弨受而讀之”,再則云“日承尊諭,以所著《五禮通考》雖巳刊刻完竣,未卽行世,恐其中或有參錯不及細檢處,須及今改訂為善。文弨學識短淺,誠知不足以副諈諉,然先生之虛懷為巳至矣,翻閱之勞所不敢辭”,則盧氏此前并未與修《五禮通考》,僅在其書成之后,勉力校訛;然其功亦巨。乾隆二十九年盧氏致書秦蕙田,為該書糾謬十五事,修訂本或采或不采,其事要皆關(guān)系重大。而盧氏貢獻仍不止此,今味經(jīng)我初刻試印本多有盧氏校語,往往溢出《復秦味經(jīng)先生校勘〈五禮通考〉各條書》所舉各條之外,有作“文弨謹案”者,當系盧氏之筆,間有作“盧云”者,未曉為何人謄錄。
而馮浩曾受邀參校,但未預(yù)其役。
據(jù)阮元為馮浩《孟亭居士文稿》所撰《序》稱,乾隆十五年馮氏參編《續(xù)文獻通考》,則亦精于典制者。其《儀禮集編小引》云:“君將赴部時,大司寇錫山味經(jīng)秦公著《五禮通考》,以參校之責屬余,余敬謝不敏,言君于秦公。”“君”即盛世佐,與馮氏為中表親、又有婚姻之誼,故馮氏薦之于秦蕙田。
另有蔣汾功、顧棟高為之作序,
據(jù)蔣《序》其“與秦氏世好:從父弱六出尊大父對巖先生之門,藥師又與予同年友也。日往來寄暢園中與其羣從子弟游。素知其家多藏書,凡禮經(jīng)疏義外間絶少刋本,而庋貯緘題者數(shù)十笥。宗伯以絶人之姿盡發(fā)而讀之。”此言秦蕙田少年時事也。
而顧氏曾就編書體例與秦蕙田往復辯難。
王大隆謂顧氏曾與秦蕙田諸人共為讀經(jīng)之會,乃顧、秦二人均無一言及此,王說恐未的。王昶《蒲褐山房詩話》云:“棟高,無錫人;鼎,金匱人,亦佐文恭纂《五禮》者。文恭嘗招予寓味經(jīng)窩數(shù)月,予病為按脈定方,故得備聞其事。”言顧氏助纂《五禮通考》,殆指秦、顧通信商討是書體例,未必謂顧參校其書也。二氏函中提及吳玉搢而未及錢大昕,則其通信當在乾隆十八、九年間,已在顧氏撰《序》之后。
三、《五禮通考》存世諸本略說
述《五禮通考》成書情實既畢,今乃就該書存世諸本略考其源流、特點,權(quán)作小結(jié)。
(一)稿本
七十三冊,殘。朱砂印格,版心刻“五禮通考卷”字樣。半頁13行,頂格者行大字21字,雙行小字21字。首蔣汾功、顧棟高二序,次凡例,次目錄二卷,次卷首存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內(nèi)有“大隆審定”白文方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朱文長方印。王欣夫《蛾術(shù)軒篋存善本書錄》著錄,今藏復旦大學。王氏《書錄》云:“此為當時清寫原稿……全書較刻本為少,當系初定本。”參本稿第一節(jié)乾隆十七、十八、十九年條。
秦蕙田《答顧復初司業(yè)論〈五禮通考〉書》云:“今所托校讎者,惟淮陰吳山夫一人,幸麤稾俱已就理。而抄胥僅有三人,不能多寫,乘此暇隙,依序詳校,討論刪潤,盡心而已,敢云著作哉?但恨卷帙大、道途遠,無由質(zhì)證耳。”《五禮通考》系絕大著作,編次謄錄不能一蹴而就,諸人皆隨錄隨改。此稿本通篇有朱筆圈點,重點語句旁勾紅圈,為后來刊本所無。眉批、夾簽滿紙,并有挖補痕跡,王氏以為休寧戴震、嘉定王鳴盛、錢大昕等手校,文字與后來刊本多不同,可見當時纂修實況。
又當時所錄不止一本。此稿本卷九七、一百一、一百三、一百五、一百九、一一四內(nèi)浮簽有“抄本”“新本”“新抄本”字樣,則此乃一舊抄本,另有新抄本,以與刊本對勘。卷一一四引《大唐開元禮》“前享五日……皆加勺冪”下,眉批“禘享以下二十四字,新抄本缺”,“二十四字”指“禘享,其未毀廟之罇坫于前楹下,各于室戶之東,皆北向西上”;“北向俱西上”下,眉批“禘又以下十四字,新抄本缺”,“十四字”指“禘又設(shè)未毀廟主各于其室,如時享”;“訖還齋所”下,眉批“禘又以下二十四字新抄本缺”,“二十四字”字指“禘又以次出,毀廟主,如主未毀廟,主出,置于室內(nèi)之座,如時享”。凡此稿本有而新抄本無之諸字,后來各本均已刪棄,可知校者但校新、舊抄本之異同,而別有人裁定當從新抄本刻印刊本。
(二)味經(jīng)窩初刻試印本
八十冊。半頁13行,頂格者行大字21字,雙行小字30字。首蔣汾功、方觀承序、次目錄二卷、次卷首四卷、次正文二百六十二卷。嘉興張廷濟、獨山莫友芝、吳興劉承干、吳縣王欣夫遞藏,后歸復旦大學。有“莫友芝/圖書印”朱文長方印,“莫印/彝孫”朱文方印,“莫友芝”、“郘亭長” (此二印《蛾術(shù)軒篋存善本書錄》未著錄)、“莫印/繩孫”白文方印、“吳興劉氏嘉業(yè)堂藏書印”朱文方印、“柳蓉/村經(jīng)/眼印”白文方印、“博古齋收藏善本書籍”朱文方印(《蛾術(shù)軒篋存善本書錄》脫“收”字)、“王欣夫藏書印”朱文長方印、“大隆審定”白文方印。張廷濟、王大隆跋語。此本亦多眉批、浮簽,王氏謂是秦蕙田、盧文弨、姚鼐手校,又云“舊粘校簽日久往往脫落,莫郘亭得此書后用墨筆移識書眉,憑筆跡可驗”。
張廷濟謂“此書審是初印底本”,良是。然王氏謂其刊于乾隆十八年(1753),不確。予舊有《味經(jīng)窩本〈五禮通考〉刊刻年代考》一稿,內(nèi)中論此本年代,略謂:
一則,此本內(nèi)參校人氏有戴震,校字者有吳玉搢。據(jù)本稿第一節(jié),吳玉搢乾隆十八年主秦宅,則此本斷不能于本年速成。而戴震明年始入都,本年尚從江永讀書于徽州紫陽書院。此本卷一百九十九“緹縞”下案語采用戴震乾隆二十二年所創(chuàng)之說,則此本年代自在其后。
再則,盧文弨乾隆二十八年所跋及明年校訂所用之本,即為此本,上有盧氏校語可證,則其年代當在此前。
以此二點相較,更證以秦蕙田《五禮通考自序》,則此味經(jīng)窩初刻試印本之刊成,當在乾隆二十六(1761)年前后,審矣。
此本與后來刊本多有不同,其差異最巨者乃卷一百九十七末尾,有一批語云:“此本較后定本少附戴氏震《勾股割圜記》五十三頁。光緒乙亥八月五日賀緒蕃記。”所謂“后定本”,即下“味經(jīng)窩修訂通行本”。
1994年,臺灣圣環(huán)圖書有限公司以拍攝膠片為底本,將此初刻試印本套彩影印,精裝八冊出版。依愚目驗,影印本與復旦原本稍有小異。
(三)味經(jīng)窩修訂通行本
此本即以初刻試印本略加改訂,吸收浮簽、眉批校勘意見,修版刊行。今各大圖書館收藏者多為此本,乃秦氏“味經(jīng)窩”刊行之最終版本。然通行各本之間實非完全一致,如通行各本卷前所載序言與每卷開列纂修人姓名即偶有不同。如上所述,顧棟高、蔣汾功、方觀承、盧見曾、王鳴盛諸人皆曾為此書作序,另有秦氏自序以及盧文弨跋文。二十六年味經(jīng)窩初刻試印本僅存蔣、方兩序,而通行各本有但存蔣、方、秦三序者,周中孚所見已如此;有存蔣、方、顧、秦四序者;有存蔣、顧、方、盧、秦五序并盧跋者。今人所編各種目錄,或不辨此本與初刻試印本之別,一誤再誤,定為“乾隆十八年本”,或據(jù)卷前所載序言年代,定為“二十六年本”、“二十八年本”。今依本稿第一節(jié),知此本刊成年代必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后。因其常見,故其后諸本都以此為祖本。
(四)四庫全書本
四庫開館后,《五禮通考》收入經(jīng)部禮類五“通禮之屬”,書前提要撰于乾隆四十三年十月(1778)。四庫本即以味經(jīng)窩修訂通行本為底本,然反復謄抄,不無訛誤,此姑勿論;尤堪注意者二事:
其一,為少數(shù)民族譯名之變更,如卷二十三引《元史·別兒怯不花傳》,文淵閣庫本改作《伯勒奇爾布哈傳》者是。
其一,為忌諱文字之刪改。四庫館寓禁于征,人所習知,乃《五禮通考》之類研經(jīng)著作,亦不能幸免,令人發(fā)指。如錢謙益,高宗甚惡其人,《五禮通考》原引錢氏文字,館臣多予抽換。卷二百六味經(jīng)窩本原引錢氏《徐霞客傳》,謂徐氏“好遠游,紀江源一篇”云云,秦蕙田案曰:“徐、李二氏論江源,一得之遠游,一得之圖象。其言皆信而有征,可補前人所未備。惟察于地理,通乎山川大原者始知之。”李指李紱,徐指霞客。今文淵閣庫本,秦案尚在,而錢《傳》已為他文所替代,與徐霞客無與也。四庫館臣之作為,真可謂顧此而失彼。
晚近臺灣商務(wù)印書館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與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更合作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及圖像檢索版)》,收錄其電子化文本,學界廣為利用。此本《五禮通考》首冊上之說明值得留意:“按:本冊原書于抗戰(zhàn)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茲雖力經(jīng)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五)清末刊本
江蘇書局本。光緒六年(1880)刊。案秦氏味經(jīng)窩刊本以軟體字付刻,錢泳視之為康乾時期版刻之佳者。此江蘇書局本版式仿味經(jīng)窩本,但字體遜色多矣。
湖南新化三味堂本。光緒二十二年(1896)刊,《三禮研究論著提要》據(jù)《四川省圖書館藏古籍目錄》著錄,尚未得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