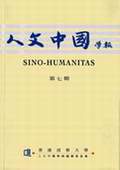
《人文中國(guó)學(xué)報(bào)》第7期
主 編:鄺健行
主 辦: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
書 號(hào):7-5325-4165-7
出 版 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shí)間:2000年4月
編輯委員會(huì):(姓氏筆畫為序)
宗靜航 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中文系
林啟彥 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歷史系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xué)歷史系
陳永明 香港教育學(xué)院
單周堯 香港大學(xué)中文系
馮耀明 香港科技大學(xué)人文學(xué)部
鄺健行(主編) 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中文系
黃國(guó)彬 香港嶺南學(xué)院翻譯系
潘銘燊 香港教育學(xué)院
鮑紹霖 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歷史系
羅秉祥 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宗哲系
顧問委員會(huì):
安樂哲 吳宏一 沈宣仁 余英時(shí) 李歐梵 周策縱 韋政通 徐中約
孫國(guó)棟 張玉法 傅佩榮 趙令揚(yáng) 劉述先 劉殿爵 謝志偉 顏清湟
本期目錄
◆論《石頭記》脂評(píng)本南北方音並存的現(xiàn)象(頁1)
香港理工大學(xué) 楊昆岡
本文從《石頭記》書中選取十八個(gè)與兒童生活有關(guān)的詞語,就其所屬方言類別、在書中使用的情況及其同義詞使用的規(guī)律,加以分析,歸結(jié)出這些詞語分屬北京話、江淮方言、吳方言和西南官話,而且其中有曹雪芹一直使用而屬於江淮方言和西南官話。明清以來,滇南的語言風(fēng)俗與南京相近,而曹氏用過的若干詞語還保留在今日的昆明話裏,故此推論曹氏用南京地區(qū)方言的語言寫作,在敍事和處理人物對(duì)話時(shí)候兼用多種方言詞語。
曹氏怕觸犯文禁,只認(rèn)是《石頭記》的編纂者,小説不確定指故事發(fā)生的時(shí)地,既突破歷代小説的陳規(guī),也為自己作了掩護(hù)。他行文瑣碎細(xì)膩,撰此一部巨著,所涉社會(huì)面廣,自然要用大量詞語,而他用詞又特別注重新奇別致的效果,講究避繁、錯(cuò)綜、音調(diào)協(xié)諧、四言成句,又重視語言與人物身份、地位、個(gè)性的一致。政治因素和藝術(shù)追求,解釋了書中南北方言詞語同時(shí)並存的緣故。
◆從「放鄭聲」看孔子刪詩說的可靠性(頁27)
香港公開大學(xué) 楊靜剛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了古代《詩經(jīng)》有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復(fù),為三百零五篇。歷代學(xué)者對(duì)此有贊成的,也有反對(duì)的,到現(xiàn)在還未成定讞,成爲(wèi)了兩千多年來的學(xué)術(shù)公案。本文嘗試從孔子自己說「放鄭聲」、「鄭聲淫」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來看孔子刪詩說的可靠性。文中首先提出古代聲(樂)、詩不分的現(xiàn)象,這在《荀子》、《墨子》、《儀禮》、《禮記》及後人顧頡剛的研究中都有説明。由於聲、詩不分,孔子既說「放鄭聲」,則鄭聲也應(yīng)在被放之列,因爲(wèi)我們不能想像只有歌詞(詩),沒有音樂(聲)的「樂歌」。但現(xiàn)在我們看毛詩,鄭詩歷歷在目,則孔子何嘗刪過詩?至於逸詩問題,本文作者認(rèn)爲(wèi)可能在《詩經(jīng)》四家之外,尚有其他版本家派,至今佚傳,只留下一些佚文佚句,為今本毛詩所無,而由先秦學(xué)者引用,得以留存。1977年安徽阜陽出土的漢簡(jiǎn)《詩經(jīng)》,或者可以證明這點(diǎn)。阜陽與四家詩都不同,不禁使人懷疑它是否四家詩以外的另一個(gè)版本。假如是的話,則逸詩的問題自迎刃而解。而最主要的,阜陽詩經(jīng)中收錄有鄭風(fēng)八首,可見不論目前所見任何版本流派,都收錄了鄭風(fēng)。由此,本文作者認(rèn)爲(wèi)孔子刪詩說是不可靠的,孔子其實(shí)並未刪過詩。
◆文人:士大夫、文官、隱逸與琴棋書畫(頁49)
首都師範(fàn)大學(xué) 楊乃喬
在古來而漫長(zhǎng)的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發(fā)展歷程中,「文人」這一話語的緣起與表達(dá)負(fù)載著厚重的歷史內(nèi)涵,「文人」作爲(wèi)「知識(shí)分子」,構(gòu)成了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中一個(gè)重要階層。在歷史上。雖然文人的思想不直接創(chuàng)造財(cái)富,但他們的思想最終可以導(dǎo)出一種令人震撼的結(jié)果,那就是,文人在執(zhí)著於信念、信仰中的創(chuàng)造並沒有直接帶來現(xiàn)實(shí)的價(jià)值而為後來者所接受,他們的價(jià)值潛在於他們的精神與生命的發(fā)展或逝去的過程中,並且,最終以他們的精神所佔(zhàn)據(jù)的百科全書式的地位而獲得權(quán)力。也就是說,最終以他們的精神與思想將凝聚在百科全書式的文本中,這種百科全書式的文本,為後來者的查找或提取意義而釋放出能量,在知識(shí)上轉(zhuǎn)換為一種權(quán)力而征服他者,但是,在中國(guó)古代歷史上,那些坦蕩、正直的文人或士大夫一旦步入官場(chǎng),他們便無法擺脫以一種情感、正直、智慧和思想來抨擊時(shí)弊或干預(yù)不公平的社會(huì),他們總是以一種神聖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與歷史使命感在天真中成就自己的自以爲(wèi)是,最終使自己陷入一種艱難的生存困境中。正是由於文人與士大夫本身所特有的這種精神氣質(zhì),因此,逃避於隱逸,逃避於琴棋書畫也成爲(wèi)文人士大夫在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史上永恒演奏的一個(gè)母題。
◆尋常詩家難相例——宗法杜韓的近代詩學(xué)意義(頁109)
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 吳淑鈿
自宋代以來,杜韓常被同時(shí)標(biāo)舉為詩學(xué)的典範(fàn),這除了意味他們有相同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外,也反映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詩學(xué)趣味。考察近代詩壇,杜韓更是廣大的詩家學(xué)習(xí)的對(duì)象,儼然成爲(wèi)中國(guó)古典詩壇最後的一個(gè)大典型。本文擬從三方面探討近代詩學(xué)宗法杜韓的意義。首先是從近代宋詩派的詩觀出發(fā),指出宗法杜韓是學(xué)人詩與詩人詩合的理想具現(xiàn),也是近代以學(xué)問性情為詩的詩論精神的總體呈現(xiàn)。其次是近代詩學(xué)既重視創(chuàng)作主體的道德修養(yǎng),反映在學(xué)古的對(duì)象上,杜韓符合詩與人合一的主導(dǎo)精神。最後是從藝術(shù)特質(zhì)及詩史地位著眼討論杜韓詩並稱的意義。通過三方面的論述。期能找出近代詩學(xué)上杜韓被認(rèn)取作為學(xué)習(xí)對(duì)象典範(fàn)的本質(zhì),及在道咸以後的學(xué)宋潮流中,杜韓以唐人仍被標(biāo)為大家的價(jià)值意義。
◆郘鐘器主再探(頁183)
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語文中心 潘慧如
郘鐘是春秋時(shí)代晉國(guó)有銘青銅器,與晚清年間在山西省出土。王國(guó)維根據(jù)銘文內(nèi)容所見之姓氏,論定郘鐘器主爲(wèi)晉國(guó)魏錡之後人,然而,近人有不同的意見,或郘鐘器主為魏錡之子魏絳,或以爲(wèi)魏錡之子魏相。本文試從史籍中所見魏氏世系,剖析後出之說並不能成立,因此,郘鐘器主的身份仍以王國(guó)維的説法為恰當(dāng)。
◆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對(duì)杜甫的研究概況(頁197)
香港浸會(huì)大學(xué) 陳少芳
本文嘗試以出版地來界定「香港」一詞之所指,並把一九四九年以後,曾在香港出版或發(fā)表過有關(guān)杜甫的論文、著作和選集等資料,加以搜索和整理,進(jìn)而從選本之述評(píng)、李杜之比較、有過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而展開的討論等不同範(fàn)疇作綜述,希望能藉此勾勒出自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在杜甫研究方面的概況。資料整理後發(fā)現(xiàn),綜觀近五十年來香港出版過有關(guān)杜甫的論文已超過一百篇,著作和選集亦不下三十多本,以香港這樣一個(gè)彈丸之地而言,成績(jī)實(shí)在令人鼓舞。而香港對(duì)杜甫的研究出了涵蓋範(fàn)圍廣泛之外,研究方法每以多層次、多角度展開,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學(xué)理論的運(yùn)用,這在提供討論問題的視野方面而言,是有其積極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