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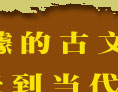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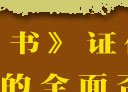

五、本文結語:閻若璩的寓言
綜上所述,閻氏《疏證》的“科學方法”絕不科學。毛奇齡“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是對閻氏方法的準確描述。胡適“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則是閻氏方法的“升華”,是侫人學術“有罪推定”原則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絕大諷刺意味的是,在《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中已經出現傾向于“無罪推定”的思想。在《大禹謨》中,皋陶對帝舜的一段話完整表述了這種傾向:“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這是一個偉大文明開創時期充滿道德和智慧的治政方略。兩種思路之間,一則博大仁愛,一則刻薄猥瑣。有多少中國學者可以區分?我們是一個什么樣文明的傳人!
本文副標題是“清代考據學存在多大問題的一次檢驗”。實際上,《古文尚書》問題貫穿中國經學史的全過程。怎么認識孔子之前《書》的性質、用途和影響?孔子是否編定過《書》?其中是否包含“二十五篇”?這“二十五篇”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三代史的史料?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什么意思?兩漢學術今古文之爭(三個世紀)在多大程度上是學術之外一邊倒的權勢利祿之爭?如果從魏晉南北朝到隋代(四個世紀)《古文尚書》對《今文尚書》的文獻替換過程是人們對二者文本質量的選擇結果,也就不存在“作偽”問題。如果事實如此,那么唐人義疏的文本選擇就是對以往四個世紀選擇結果的正確和重要的確認。這就有必要重新認識和評價唐代學術在中國傳統學術史中的意義和地位。
宋代學術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孟子風格”,《大禹謨》“十六字心法”以唐人文本選擇為前提,朱熹對“二十五篇”行文平易的“猜想”則是對同一前提的逆反。“懷疑精神”在學術史中絕非壞事,關鍵問題是清代學術對朱熹“猜想”給出了一個什么樣的研究結果。本文至少可以證實閻若璩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但是,閻氏的方法和結論卻在一定程度上為此后的清代學術提供了依據,包括乾嘉考據對“漢學”的復古,包括“古文學”和“今文學”的興替。閻氏之后清代考據學被稱作“漢學”,江藩將閻若璩列為清代“漢學家”第一人。事情開始有些荒唐:考據學鼎盛時期為什么無力糾正閻氏《疏證》中大量十分明顯的考據錯誤?清代“漢學”古文家、今文家的學術定位有幾分明白幾分糊涂?兩個世紀清代學術在多大程度上以閻氏《疏證》為支點?
閻若璩在《疏證》中(第八十)講了一個故事。先說鄭康成于病重時以書信告子:“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多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然後講他自己“《疏證》第五卷寫成,年五十有三”。再說卜葬其父的過程。最后說:“后三年,果有……善寫生者適至,屬寫二圖,一禮堂寫定圖,一傳與其人圖。觀者咸嘆其秀眉明目,以為康成遺照,而不知實以余像代之。因藏諸丙舍秋山紅樹閣,視我世世子孫云。”
鄭玄書信見《后漢書》本傳。“末所憤憤者”是鄭玄于病重時交待遺愿。“其可圖乎”是囑其子設法了卻暮年心愿(和畫像沒有關系)。我讀《疏證》三遍。初見上文,哂其誤解文義,行事荒唐;連“秀眉明目”〔68〕都要掉書口袋。復見,觀其自比康成,沐猴而冠,竊竊私喜之狀。三讀,驀然警醒,終于覺察到他移花接木、惡意戲弄的快感:我逗你們玩兒吶。《疏證》五卷寫成,他已經蜚聲海內。這就怪不得他敢于寫下這樣的寓言。大約在此之后,他開始往《疏證》中“注水”。
由于閻氏寓言戲弄成分過于露骨,被他孫子閻學林在集資所刻西堂本中刪掉。其動機是對家祖的溫情與敬意。閻氏之后,中國一些知識精英逐漸喪失對中國文明的溫情與敬意。歷史學家最終成為歷史的殺手。這樣的歷史研究轉化為酷吏斷案深文周納的筆墨文書。“莫須有”的作偽故事如此這般編造下來,形成一種極不審慎的惡劣學風,于是有了康有為先生的作偽故事(《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顧頡剛先生的作偽故事(“層累”說)。于是一些今文《尚書》篇章和更多的古文獻也最終成為“偽書”。
時至今日,中國史學界似乎仍然搞不清楚誰是歷史學家,誰是佞人遺種,什么叫客觀慎重的科學研究,什么叫酷吏斷案的筆墨功夫。一門健全的學科必須要有一個知識的輪廓,要有一套獲得和分析經驗的相對成熟的方法,一套修復謬誤和良性生長的機制。難道沒有地下出土的“物證”,我們就沒有能力解決問題?
說來有些荒唐,實則大可悲哀。
〔1〕黃宗羲:《尚書古文疏證·序》。
〔2〕《四庫提要·四書釋地》。按據《清史稿》本傳,《四庫提要》為紀昀所撰。具體是在“分纂稿”基礎上考核刪定而成。
〔3〕《四庫提要·尚書古文疏證》。
〔4〕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陳引馳編校《梁啟超國學講錄二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頁。
〔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頁。
〔6〕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頁。
〔7〕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見《胡適文存》三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94頁。
〔8〕顧頡剛:《古今偽書考·序》,見《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253頁。
〔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78頁。
〔10〕同上書,第257頁。
〔11〕同上書,第277頁。
〔12〕同上書,第272頁。
〔13〕同上書,第273頁。
〔14〕同上書,第268頁。
〔15〕同上書,第276頁。
〔16〕同上書,第277頁。
〔17〕同上書,第250頁。同上書,第272頁。
〔18〕《疏證》第九條。
〔1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72頁。
〔20〕同上書,第272頁。
〔2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古文尚書疏證》。
〔2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68頁。
〔23〕顧頡剛:《古史辨》第三冊《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24〕《中州學刊》2000年第2期。
〔25〕《聊城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
〔26〕《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故為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閑。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27〕《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懷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孔安國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28〕《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
〔29〕《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30〕《漢書·藝文志》。
〔31〕《漢書·儒林傳》:歐陽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32〕《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谷梁《春秋》博士。
〔33〕《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34〕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44頁~47頁。該書對此有較深入討論,可參閱。
〔35〕王國維:《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89~190頁。
〔36〕《疏證》第一百六。
〔37〕〔38〕〔39〕《漢書》本傳。
〔40〕《漢書·藝文志》記劉向以中古文(孔壁本)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伏生本),其間脫簡、脫字以及文字互異者約有八九百字。由此可知,“孔壁本”的保存質量要明顯好于“伏生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比較了三個《尚書》版本(孔壁本、伏生本及馬鄭注本),明確指出:今文《尚書》(伏生本)“闕謬處多”。
〔41〕從漢武帝采納公孫弘建議“為博士官置弟子(《史記·儒林列傳》)”并建立教學、考試和“以文學禮義為官(同上書)”的任官制度,“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同上書)”。《漢書·匡張孔馬傳贊》:“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后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從“孝武興學”到西漢末期,僅“以儒宗居宰相位”者便有十余人,等而次之者更是不計其數(可參閱王國維《漢魏博士考》)。今文經博士官把持朝政,其勢力盤根錯節,長盛不衰。
〔42〕《隋書·經籍志》:《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十一卷,王肅注。
〔43〕《隋書·經籍志》具體有:“《一字石經尚書》六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
〔44〕《后漢書·杜林傳》。按后世研究者多以為杜林漆書“一卷”篇幅“裝”不下賈馬鄭本的內容。《后漢書·儒林傳》記“董卓移都之際”皇家藏書“典策文章”散亂流失情況:“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杜林所得漆書一卷如果是可以“連為帷蓋”之大者,其容量裝下賈馬鄭本內容綽綽有余。
〔45〕參閱《尚書正義·堯典》。
〔46〕張巖:《從部落文明到禮樂制度》,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5月,序言部分,第5頁~第15頁。
〔47〕參閱王國維:《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202~205頁。
〔48〕《疏證》第十七。
〔49〕參看李學勤:《論魏晉時期古文〈尚書〉的傳流》。楊善群:《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學習與探討》,2003年,4期。
〔50〕據顧頡剛主編《尚書通檢》,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
〔51〕參看楊善群:《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學習與探討》,2003年,4期。
〔52〕《隋書·經籍志》: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并行,而鄭氏甚微。自余所存,無復師說。
〔53〕《新唐書·孔穎達傳》: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余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
〔54〕《舊唐書·孔穎達傳》。
〔55〕見注〔43〕。按王國維《觀堂集林·魏石經考三》推測《隋書·經籍志》載《三字石經尚書》“足本”當為“十三卷”。由于史料不備,此事已經很難搞清。
〔56〕見注〔42〕。
〔57〕〔58〕孔穎達:《尚書正義·序》。
〔59〕按唐代以后,賈、馬、鄭、王四家注本逐漸散失,但四家注文很大一部分內容(大約五六百條)被集中保留在孔穎達《尚書正義》內,其中鄭注最多,馬次之,王次之,賈最少。
〔60〕《漢書·儒林傳》。
〔61〕孔穎達《疏》:“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后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62〕按王國維《古史新證》(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影印。第285~286頁)認為殘碑“無祖甲而有太宗”。
〔63〕主要保留在“《史記》三家注”中。
〔64〕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6頁。
〔65〕朱彝尊:《曝書亭集·尚書古文辨》。
〔6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75頁。
〔67〕楊善群:《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齊魯學刊》2003年,第5期。
〔68〕《后漢書·鄭玄傳》。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網總編室 010.68900123轉808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