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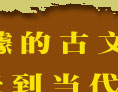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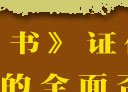

四、《疏證》偽證考略(下)
(5)虞廷十六字
“虞廷十六字”(《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被宋儒奉為歷圣相傳的心法、道統,成為宋明理學中最重要的理論根據。因此,閻氏對此“辨偽”的影響頗大。至今時常有人提到。《疏證》(第三十一):“二十五篇之《書》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其精密絕倫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證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滅虞廷十六字為烏有,猶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蓋純襲用《荀子》,而世舉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遂隱括為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偽古文蓋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謨》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讀之,引‘無有作好’四句則冠以‘《書》曰’,引‘維齊非齊’一句則冠以‘《書》曰’,以及他所引書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則明’,冠以《康誥》。引‘獨夫紂’則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誥》亦然。豈獨引《大禹謨》而輒改,目為《道經》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經》,而偽古文蓋襲用,初非其能造語精密至此極也。”
前面說過,“太甲稽首于伊尹”一節已被閻氏自行刪掉。留在此處亦屬虛張聲勢。很明顯,這一條也是經過駁難后的調整。其主要內容是:(1)指出“十六字”是抄襲《荀子》。(2)有人對此提出駁難:“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謨》之文”。(3)閻氏的反駁。反駁理由是:《荀子》引《書》均冠以“《書》曰”或篇名,“獨引《大禹謨》”改為《道經》,所以是“偽古文”抄襲《荀子》所引《道經》。從邏輯上說,閻氏這一反駁是否成立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第二個類似情況(例外)——凡《荀子》引《書》均交待了(正確的)出處,唯獨引《大禹謨》“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卻說出自《道經》——只要有第二個例外(反證),其結論就不能成立。由駁難者提出的兩個相反證據極有分量,卻被他排除在正面論述之外。他在此使用的伎倆仍然是將相反證據(例外)“藏”在后面的按語中。
《疏證》后文提到駁難者提出的相反證據:“按《荀子》引今文、古文《書》者十六,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作‘《傳》曰’。‘《傳》’疑‘《書》’字之訛。然《孟子》‘于《傳》有之’亦指《書》言也。”(第三十一)這分明就是第二個例外(反證1)。首先,“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出自《尚書》今文篇章《呂刑》。其次,《荀子》此處雖然交待了出處,但卻是一個錯誤的出處。閻氏對此的第一個辯解是指出《荀子》誤《書》為《傳》是訛誤的結果。依據同一個判斷規則,《荀子》誤《大禹謨》為《道經》同樣可能是訛誤的結果!第二個辯解是指出“《孟子》‘于《傳》有之’亦指《書》言也”,《傳》和《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孟子》此處實為《荀子》之外的另一個例外。故閻氏兩個辯解都屬于毫無道理的狡辯。
《荀子·王制》:“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后我也!’”上文是《荀子》中又一個例外(反證2)。《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對(齊宣王)曰: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比較《孟子》內容可知,《荀子》上文是引《尚書》內容(實為古文篇章《仲虺之誥》),但沒有交待出處,且敘事有誤(張冠李戴:誤商湯為周公)引文也與原文頗有出入(《尚書·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由于兩個相反證據的存在,不能排除《荀子》搞錯了引文出處(包括引文內容的不準確)。因此,閻氏這一條的“證據”沒有“證明力”,論證過程存在明顯作弊行為,結論完全不能成立。
《疏證》后文(第三十二)又提出另外一組“證據”:“‘人心’、‘道心’本出《荀子》,以竄入《大禹謨》,遂尊為經,久而忘其所自來矣。竊以古今若此類者頗多,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列子》引《黃帝書》也。今見《老子》上篇‘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引《周書》也,亦見《老子》上篇,今孰不以為此老子語與?‘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出《淮南子·主術訓》,而諸葛武侯引以戒其子,今遂為武侯語。‘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亦出《淮南子·主術訓》,而孫思邈引之,而程子稱之,今遂為孫思邈語。不獨此也,《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云云,河間獻王作《樂記》采之,今且為經。是即以子為經之證也。《荀子》有《禮論篇》,今自“三年之喪,何也”?至‘古今之所,一也’一段,載入《禮記》,名曰《三年問》。是又即以《荀子》為經之證也。而必以‘人心’、‘道心’為無本焉,亦過矣。”
說“古今若此類者頗多”的前提條件,需要先完成“‘人心’、‘道心’本出《荀子》”的確證過程。且不論閻氏上述幾個引文、原文關系是否全都可靠。在沒有確鑿證據證明一個人(甲)是賊的情況下,別人(乙、丙、丁……)的盜竊行為是否可以證明此人(甲)也是賊呢?如果已經證明“‘人心’、‘道心’本出《荀子》”,則這一條純屬廢話。實際上根本沒有可靠的證明過程,則“古今若此類者頗多”不過是誣陷的借口。閻氏這兩條(第三十一、三十二)論證相當拙劣,按道理應當刪掉。但前面他已經刪掉三條(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再這樣刪下去最后恐怕只剩下“支蔓”。刪還是不刪對他來說是一個問題。
有人建議他刪——“或問余:人之論議先后容有互異,子書尚未成,何不舉前說之誤者而悉削之,而必以示后人乎?”(《疏證》第三十二)他錯了也不刪居然還有道理——“余曰:此以著學問之無窮而人之不可以自是也(同上)”。因他人正確的批評而修改己說在他看來是一種不正確的行為——“近見世之君子矜其長而覆其短,一聞有商略者,輒同仇敵(同上)”。只要你批評我,你就是我的“仇敵”。這個邏輯十分可怕。由于錯了也不刪(實際上他私下里刪了不少)他屢遭物議:“余用是數困于世(同上)”。
這種情況令他非常惱怒。于是他說出下面一段十分朦朧的話:“昔王荊公(王安石)注《周禮》‘贊牛耳’云:取其順聽。有人引一牛來,與荊公辯牛之聽不以耳蓋以鼻,荊公遂易前《注》。以荊公之執拗文過,古人中無兩,猶不能不屈服于引牛者之言,吾不知世之君子,自視于荊公何如也(同上)。”此事出自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四。王氏講述這個荒唐故事的動機已經搞不太清楚,閻若璩復述這個故事的目的則是為了罵人。他的罵人風格富于變化,“刳心著地,與數斤肉相似”(第七十五)走陽剛一路,前面提到“孔明言碎”則陰柔婉轉。“牛以鼻聽”更加婉約刻毒,飄忽費解。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網總編室 010.68900123轉808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