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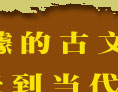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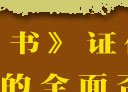

四、《疏證》偽證考略(下)
(2)孔注《論語》《尚書》比較
紀昀《四庫提要·尚書正義》一共提到四條作偽證據。除上面已經討論過的三條地理方面的證據外,第四條由閻氏提出:“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錢穆先生曾批評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對《疏證》的駁難“非要點”:“此謂乘瑕蹈隙,避堅攻脆,乃兵家之詭譎,非辯難之正宗。”〔66〕為避免此類批評,我在本文主要選擇《疏證》中最關鍵的問題,避脆攻堅,折其鋒鍔。閻氏這一條證據與上面已經討論過的三條地理方面的證據一樣,不僅被紀昀《四庫提要》特別提出,而且至今為止一直是經常被人們提到的重要“鐵證”之一。因此有必要作正面討論。
《疏證》(第十九):“漢傳《論語》有三家:一魯論,一齊論,一古論。古論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馬融、鄭康成注皆本之。《藝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是也。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國之辭。余嘗取孔注《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四句,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一句,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浩》《泰誓》《武成》,豈有注《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為乖剌至于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為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注《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于裨諶、子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篽縷陳之于《注》,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為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又斷斷也。”
《疏證》這一專題凡三千余字,上文是對主要問題的正面論述。其要點如下:(1)安國曾注《論語》。(2)閻氏“取孔注《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發現孔注《論語》“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3)因此“晚出古文”《湯誥》《泰誓》《武成》“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所得”,換言之是后人偽造。這一條從證據到論證都十分精彩,具有非常強的說服力,是《疏證》中最炫人心智的論證之一。閻氏此條“靈感”來自《論語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中邢昺的兩段說明。
邢昺第一個說明是解釋孔注《論語》為什么要說“《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的原因:“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為伐桀告天之文也。”邢昺是在作出比較后得出的結論,下面是他的三個比較對象:(1)《論語·堯曰》內容:“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2)《墨子·兼愛下》相關內容:“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3)《尚書·湯誥》相關內容:“肆臺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邢昺認為,相對來說三者間《論語》和《墨子》內容更加接近。事實也的確如此。所以他認為孔安國在作了相同比較之后,于孔注《論語》中得出“《墨子》引《湯誓》(《墨子》原文是《湯說》),其辭若此”的結論。邢昺的比較和分析并非沒有道理。這里本來風平浪靜,沒有什么問題。天有不測風云,忽一日,過來一位叫做閻若璩的人,他的專長就是“旁搜曲引,吹毛索瘢”。他立刻“發現問題”。但是,他在正面陳述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對“問題”出處,包括邢昺的比較過程,三個比較對象的異同關系,他絕口不提!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據古文則‘予小子履’等語,正《湯誥》之文也。作《論語》者,亦引《湯誥》,而孔不曰‘此出《湯誥》’,或曰‘與《湯誥》小異’。而乃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何其自為乖剌至于如是其極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注意,《論語》和《墨子》都是“予小子履”,《湯誥》則是“肆臺小子”,不是“予小子履”!這正是孔穎達所謂“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是明顯的作弊。
邢昺第二個說明是解釋孔注《論語》與《泰誓》不同的原因:“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河朔誓眾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伐紂誓眾之辭,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閻氏在此的作弊手段,仍然是絕口不提邢昺的說明,并反其道而行之:“又從來訓故家于兩書之辭相同者,皆各為詮釋。雖小有同異,不至懸絕。今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書》‘周親仁人’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且安國縱善忘,注《論語》時,至此獨不憶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語勢皆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
孔安國先注《論語》,后注《尚書》,后注比前注更加準確。孔注《論語》(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一語中并不含有閻氏所謂“周之才不如商”的意思。因此,兩個注語間不存在含義的“懸絕”關系。這種隨文就注小有抵牾的現象不足為奇,前面提到《疏證》本身也存在遺忘疏漏問題。從邏輯上說,兩個注語之間略有不同的現象與是否作偽沒有關系。再者,何晏《論語集解·序》講得很清楚:“今集諸家(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等)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也就是說,何晏集解《論語》并非對諸家注的原文照錄,而是有所取舍。這個取舍和“頗為改易”過程的存在,進一步削弱了閻氏證據的證明力。
下面是《論語注疏》中何晏《論語集解》的內容:“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權,秤也。量,斗斛。)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上面的正文是《論語》內容,括號中是何晏《集解》內容。閻氏故意忽略的部分是“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及其后面的注文。《尚書·武成》(古文):“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孔傳注此句曰:“施舍已債,救乏周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這正是孔安國先注《論語》,后傳《尚書》的結果。《武成》后文“崇德報功”與“善人是富”相呼應,表明《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是在概述《武成》內容。《尚書正義·武成》孔穎達《疏》對此的解釋是:“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
再來比較下面的內容:孔注《論語》(所重民食喪祭)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孔注《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曰:“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圣王所重。”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呼應關系。怎么能說是“絕不類”呢?有必要強調指出,閻氏在三千余字的專題論述中,完整引錄上面孔注《論語》內容,對于孔注《武成》內容則只字不提。也就是說,他在行文中“假裝”作了完整比較,實際上他把對自己結論不利的內容“忽略”掉了,然后給出一個好像很合理實際上不能成立的結論。換言之,他在論證過程中剝奪了閱讀者自行比較的條件。除非有人想去翻閱原文。這在當時不太方便。
在“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間,注曰:“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這一條注語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既注解了前文,又關照了后文。“有亂臣十人”是《泰誓》(古文)中的語句,“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也是。二者在《泰誓》原文中前后關聯:“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由此可以基本確認,這一段文字的注釋者讀到過《古文尚書·泰誓》。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
第一,“可以基本確認”這一段文字的注釋者讀到過《古文尚書·泰誓》的理由。《論語·泰伯》提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但這句話的意思及其前后文與“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沒有直接關系。在沒有看到《古文尚書·泰誓》原文的情況下,注釋者碰巧將其引到這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微乎其微。《左傳》“亂臣十人”兩見(襄28、昭24),但沒有“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一語。因此,碰巧引過來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
第二,這一段文字的注釋者是誰。何晏《論語集解·序》:“今集諸家之善者,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后文提到具體的注釋者共有五人(孫邕、鄭沖、曹羲、荀顗、何晏)。刑昺《論語疏》:“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晉書·鄭沖傳》:“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等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正始中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論語集解》匯集以往諸家注解,經過選擇和改易編撰而成。由何晏主持編撰,鄭沖等四人參加,共同完成于正始年間(241~249)。刑昺《論語疏》:“頗為改易者,言諸家之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為改易之。注首不言包曰、馬曰,及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言、改易先儒者也。”
由此推測,上述一段注釋的來歷有兩種可能。一是被改易的舊注。上面所引一整段《論語集解》中共有十二條注文,孔安國(孔曰)六條、包咸(包曰)三條、無名注三條。如果是被改易的舊注,是孔注的可能性很大。二是何晏等五人“自下已言”。第二種情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是第一種情況,說明《古文尚書·泰誓》在此前早已流傳于世。如果是第二種情況,何晏等五人應讀到過《古文尚書·泰誓》,其中包括鄭沖。這就呼應了《尚書正義·堯典》孔穎達《疏》引《晉書》關于《古文尚書》傳授情況的記載:“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論語集解》的開始編撰有可能略早于魏正始年間(241~249),《古文尚書》的開始流傳也應略早于此。也就是說,這一條證據還可以為王肅(195~256)注《尚書》時見到孔傳《古文尚書》提供比較可靠的依據。因此,這是一條有關《古文尚書》早期流傳情況十分重要的間接證據。這條證據如果被“發現”,不僅《疏證》第十九條三千余字的全部論證會因此失去意義、他的“品質問題”會有所暴露,還會對《疏證》全書的合理性構成威脅。所以他絕口不提,諱莫如深。綜上所述,閻若璩這一著名證據不但不像紀昀所說“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反而是一條經過一系列作弊步驟強行提出的偽證。其提出條件非常勉強,但炮制的水平相當高超。這個作弊過程恰可體現“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的準確含義,同時也體現了此人內心十分陰暗的一面。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網總編室 010.68900123轉808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