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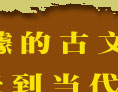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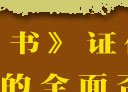

三、《疏證》偽證考略(中)
(4)虞夏書之分
《疏證》“證偽”專題之一是兩漢至魏晉今古文《尚書》諸傳本的篇卷劃分。其中,“《虞書》《夏書》之分”是一重要證據(jù)。《疏證》(第四):“《虞書》《夏書》之分,實(shí)自安國傳始。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孔穎達(dá)所謂‘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是也。即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鄭康成《序》又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余觀揚(yáng)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shí)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杜元?jiǎng)P《左傳注》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三句,注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shí)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為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后《書》題卷數(shù)篇名盡亂其舊矣。”閻氏此條基本思路是:如果“東晉梅氏《書》出”之前沒有“《虞書》《夏書》之分”,“梅氏《書》”的這一劃分就是作偽證據(jù)。
上文共提出五條證據(jù)。前三條來自《尚書正義?堯典》孔《疏》:“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夏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于《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dāng)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guān)禹,故引為《夏書》。”
孔穎達(dá)上文分析《虞書》、《夏書》分合問題提到兩種情況:其一,東漢馬鄭注本皆曰“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其二,孔傳本“虞、夏別題”。所謂“虞、夏同科”,是伏生今文《尚書》“學(xué)官”講學(xué)時(shí)將《虞書》、《夏書》劃入同一“教學(xué)單元”,故合稱《虞夏書》;此即鄭玄所謂“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但是,這種情況并不說明先秦、兩漢乃至西晉沒有《虞書》、《夏書》的劃分。比如,先秦文獻(xiàn)引《書》“無并言《虞夏書》者”;又如,《左傳》引《書》多有區(qū)分《虞書》(文18)、《夏書》(莊8、僖22、僖27、襄26等)的例證,只是在分法上與孔傳本有所不同。伏生《尚書大傳》介于二者之間,在合的角度有《虞夏傳》,在分的角度又有《虞傳》和《夏傳》。兩漢間立于學(xué)官的《尚書》今文諸家(歐陽、大小夏侯等)同出伏生之學(xué),因此這種既有分、也有合的現(xiàn)象是一個(gè)過渡點(diǎn):此前只有分,沒有合;此后既有分,也有合。揚(yáng)雄《虞夏之書》、杜預(yù)《虞夏書》是合稱,許慎《說文》“于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則是“別題”。
由于上述情況,孔穎達(dá)并未在分合之間強(qiáng)作非此即彼的判斷;他認(rèn)為兩種情況都存在,事實(shí)也的確如此。用閻若璩自己的話說,“學(xué)者試平心以思”,在孔穎達(dá)的征引和分析中并不存在可以拿來“證偽”的線索。閻氏的前提是“有罪推定”,強(qiáng)執(zhí)一端,他在“書縫”中找到這條“證據(jù)”十分勉強(qiáng),為此他在文字上頗下了一番功夫。比如,孔穎達(dá)說“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閻氏改作“即伏生《虞傳》《夏傳》外,仍有一《虞夏傳》”;伏生《尚書大傳》既有“分”、也有“合”的情況實(shí)際上是閻氏判斷的否定證據(jù),如此顛倒語序可以淡化“分”而強(qiáng)調(diào)“合”,產(chǎn)生一種邏輯誤導(dǎo)效果。但畢竟不能抹殺“分”的存在。因此,這一條證據(jù)實(shí)際上也是捏造出來的。
如果說伏生《尚書大傳》的分、合情況已經(jīng)使閻氏捉襟見肘,那么許慎《說文》的“反證”則足以推翻其立論。他分明知道這條“反證”的存在,并在后文中提到──《疏證》(第七十八):“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肅、鄭康成古文以上,統(tǒng)名《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茲《說文》于引今《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于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唯于今《舜典》‘五品不遜’作《唐書》,與《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同。四引《洪范》皆曰《商書》,與《左氏傳》同,卻與賈氏所奏異。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
他對(duì)這條“反證”可以擊中其要害的情況十分清楚。為此他又作了一些手腳:一是將“反證”與正面討論內(nèi)容分開,將正面討論放在顯要位置,將反證“隱藏”在一個(g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支蔓”的用處);二是岔開話題,以攻為守:“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三也是以攻為守,對(duì)“反證”提出質(zhì)疑:“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如果是一個(gè)在學(xué)術(shù)上還有一點(diǎn)品位的人,既已知反證的存在,也就不會(huì)強(qiáng)行立論;若是事后知道,可以用刪除加以修正。他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作了一系列捏造證據(jù)的手腳──顛倒語序是耍了一個(gè)小聰明,將反證分開并“藏”起來則頗有心計(jì),岔開話題以攻為守已是無賴手段。
北京國學(xué)時(shí)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xué)網(wǎng)總編室 010.68900123轉(zhuǎn)808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