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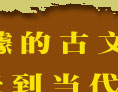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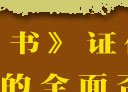

二、《疏證》偽證考略(上)
(4)誰是作偽者
《疏證》方成四卷,黃宗羲為之作序提到:“梅賾作偽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偽。”黃氏理解力不應(yīng)有問題,故《疏證》最初以為“梅賾作偽書”。今本《疏證》對此語焉不詳(第十七):“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jì)》。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沖,鄭沖以上則無聞焉。嗚呼,其果安國之舊耶?抑魏晉之間假托者耶?”皇甫謐(215~282)《帝王世紀(jì)》多處引用《古文尚書》和《孔傳》內(nèi)容〔48〕。梅賾獻(xiàn)書時(大約317~318年)皇甫謐故去三十余年,故閻氏在黃宗羲作序后改變說法。不再強(qiáng)調(diào)“梅賾作偽書”,只說“魏晉之間假托者”。至于“作偽”過程,他認(rèn)為是“個人行為”(《疏證》第八十六):“《書》與《傳》同出一手”。我曾對《古文尚書》(二十五篇)真?zhèn)螁栴}作過一些具體分析〔49〕。
比如,《古文尚書》“引文”、“用文”情況。先秦乃至漢代文獻(xiàn)引《書》,今文和古文篇章大體相同;一字不差引用原文者不足一半,大多在原文與引文間有所不同,包括字句缺省、語句顛倒錯亂和對原文意思的概述;這與“借字”情況相似(提筆忘字,手頭沒有字典,只好寫個錯白字),是記憶不準(zhǔn)、沒有核對原文和缺少“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的結(jié)果。此外,還有一些不以“書曰”等方式正面引用,或行文用其詞語,或以《尚書》中一些觀念、禮制為本展開論說。上述第一種情況可稱“引文”,第二種情況可稱“用文”。
證偽者主要方法之一,是在文獻(xiàn)中尋找古文篇章引文、用文例證,將其用為作偽證據(jù)。具體思路是魏晉間某人遍查群書,廣泛收集引文、用文的文獻(xiàn)內(nèi)容,在此基礎(chǔ)上連貫字句、拼湊偽造“二十五篇”。這里的問題是,古文篇章引文、用文種種情況今文篇章同樣存在。在今文篇章,人們知道這是原文和引文、用文的關(guān)系,這一現(xiàn)象恰可證明原文的存在和影響;同樣的現(xiàn)象對古文篇章也應(yīng)具有相同的證明意義。相同的素材和思路不應(yīng)得出相反的結(jié)論。這一證偽途徑存在明顯邏輯錯誤,不能構(gòu)成有效的證偽依據(jù)。《疏證》約有一半內(nèi)容走此一路,深文周納,強(qiáng)詞奪理(后面舉例說明)。
二十五篇《古文尚書》約7600字,其內(nèi)容精致典雅,在文化觀念和禮樂制度方面與今文篇章彼此呼應(yīng),除行文流暢一些,并無明顯作偽痕跡。現(xiàn)已考知出處的先秦文獻(xiàn)“引文”約有一百二十條,先秦兩漢文獻(xiàn)“用文”情況更遠(yuǎn)多于此。以《大禹謨》為例,先秦引文約十七條,自先秦至魏晉文獻(xiàn)中用文情況超過一百條。這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古文篇章中存在許多自先秦至魏晉文獻(xiàn)中的罕見詞語,在這個時段大量文獻(xiàn)中出現(xiàn)三次以下的詞語,僅《大禹謨》就有六十余處。有兩種可能,一是作偽者刻意收集罕見詞語,用為作偽“材料”編入文中;二是《古文尚書》雖非顯學(xué)畢竟存在,這些罕見詞語屬于“用文”。前者難度太高且沒有必要。西漢以降形成一種“擬古文風(fēng)”,即在一些書寫場合多采用對先秦文獻(xiàn)尤其是經(jīng)典文獻(xiàn)的引文、用文。許多罕見詞語正是出現(xiàn)于這種場合。因此,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yuǎn)高于前者。
再如,在文化觀念和禮樂制度方面,古文篇章不僅與今文篇章彼此呼應(yīng),還與先秦乃至兩漢文獻(xiàn)中的大量內(nèi)容間存在呼應(yīng)關(guān)系。后一種呼應(yīng)中多有“一呼百應(yīng)”的特征。即古文篇章中片言只語提到的觀念和制度往往成為其后文獻(xiàn)中多次出現(xiàn)的議論主題。這里也有兩種可能,一是作偽者博覽群籍,區(qū)分主次,總其樞要,約其文辭,編入書中;二是《尚書》作為非常重要的經(jīng)典文獻(xiàn),故有一呼百應(yīng)的影響。假如存在一個作偽者,他當(dāng)然希望實(shí)現(xiàn)這樣的作偽效果,只是難度過大。若確有此人此事,后世治學(xué)術(shù)思想禮制史的學(xué)人罕有望其項(xiàng)背者。上述現(xiàn)象今古文篇章同樣存在,故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yuǎn)高于前者。
又如,“字頻”問題。今古文《尚書》約24600字,去其重復(fù),約使用1900余字〔50〕。某些字在不同時代和文獻(xiàn)中的用字量(現(xiàn)代語言學(xué)研究中所謂“字頻”)明顯不同,這與不同時期、不同文獻(xiàn)的具體內(nèi)容、語法習(xí)慣和撰寫風(fēng)格有關(guān)。在文獻(xiàn)的長期流傳和古今字體的轉(zhuǎn)換中會出現(xiàn)少量改字,但不會影響用字量不同的整體情況。我曾專門作過一次檢索和對比分析。檢索范圍是《尚書》和先秦兩漢另外二十余種參照文獻(xiàn)(《詩》《逸周書》《易》《周禮》《國》《左》《論語》《孟》《荀》《禮記》《管子》《晏子春秋》《墨》《老》《列》《莊》《鹖冠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新書》《說苑》《論衡》《史記》《漢書》等)。
具體步驟是先通過初步判斷選出五百余字,在上述每種文獻(xiàn)中檢索每個字的出現(xiàn)次數(shù),再換算成每個字在每種文獻(xiàn)中的萬字含量,然后在萬字含量的一萬多個數(shù)據(jù)間進(jìn)行對比,選出《尚書》與其他參照文獻(xiàn)萬字含量(或多或少)明顯不同的108個字,姑且稱其為“《尚書》用字量特征字群”。這108個字多是《尚書》中的常用字,其重復(fù)使用數(shù)量約占《尚書》總篇幅三分之一,其中“多字組”(100字)的萬字含量比其他參照文獻(xiàn)萬字含量平均多出一倍以上(5﹕1),“少字組”(8字)萬字含量比其他參照文獻(xiàn)平均少了一倍以上(10﹕29);在今文篇章和古文篇章之間進(jìn)行對比,這108個字在二者間的平均萬字含量基本一致(今文47%﹕53%古文)。
先說“多字組”的情況。比如:(1)“乃”字,在《尚書》中的萬字含量是148字,在參照文獻(xiàn)中的萬字含量是26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的比例是142字﹕150字;(2)“惟”字,《尚書》萬字含量是263字,參照文獻(xiàn)是2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330字﹕233字;(3)“永”字,《尚書》萬字含量是20字,參照文獻(xiàn)是1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24字﹕19字;(4)“若”字,《尚書》萬字含量是69字,參照文獻(xiàn)是2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68字﹕69字;(5)“厥”字,《尚書》萬字含量是129字,參照文獻(xiàn)是2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157字﹕117字;(6)“作”字,《尚書》萬字含量是58字,參照文獻(xiàn)是1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58字﹕58字。
在兩漢魏晉間文獻(xiàn)中,“多字組”文字(如:疇厎誕怠孚厥緝克暨僉懋惟詢矧允攸愆爰等)的出現(xiàn)次數(shù)一方面明顯少于《尚書》,另一方面大多出現(xiàn)于前面提到具有明顯“擬古文風(fēng)”的書寫場合,其前后文多有“引文”、“用文”現(xiàn)象(或其本身便在引文、用文中)。這里也有兩種可能,一是作偽者刻意實(shí)現(xiàn)了這種“天衣無縫”的作偽效果;二是今古文篇章都是真文獻(xiàn),故用字量特征相同。為實(shí)現(xiàn)這種效果,作偽者(如果真有這么一個人)在“偽造”古文篇章過程中,每三個字中要考慮一個字的萬字含量,使其出現(xiàn)率同步于今文篇章。為此,他必須對“《尚書》用字量特征字群”在先秦兩漢文獻(xiàn)中的萬字含量有一個比較準(zhǔn)確的了解。我完成上述檢索過程,雖借助電腦的文檔檢索功能(word“替換”),仍然用了三個多月(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極其單調(diào)繁瑣。
如果不借助電腦檢索的字?jǐn)?shù)統(tǒng)計功能,完成此過程要對總篇幅幾百萬字的幾十種文獻(xiàn)一絲不茍地閱讀(統(tǒng)計)幾百遍,還要將由此獲得的上萬個數(shù)據(jù)經(jīng)過兩步計算(某字在某文獻(xiàn)中的出現(xiàn)次數(shù)÷該文獻(xiàn)總字?jǐn)?shù)×10000)轉(zhuǎn)換為萬字含量。從收集文獻(xiàn)到完成閱讀統(tǒng)計和換算,僅此一項(xiàng),以一人之力至少要用二十余年時間。據(jù)我所知,“字頻統(tǒng)計”是近代以來語言學(xué)研究中比較新穎的方法,隨著計算機(jī)的普及逐漸被研究者采用。我國古文獻(xiàn)研究中采用這種方法更晚一些。魏晉之間也就是一千七八百年前那位“作偽者”居然能夠嫻熟使用這項(xiàng)如此晚近的研究方法。這可能嗎?
作偽者最難實(shí)現(xiàn)的效果之一,是古文篇章“少字組”文字(行可相則能所之為)的出現(xiàn)率同步于今文篇章。因?yàn)椋渲幸恍┳衷凇渡袝分械某霈F(xiàn)率較高,在參照文獻(xiàn)中的出現(xiàn)率更高,需要在“較高”和“更高”之間拿捏分寸。比如:(1)“之”字,在《尚書》中的萬字含量是137字,在參照文獻(xiàn)中的萬字含量是367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間萬字含量的比例是141字﹕136字。(2)“可”字,《尚書》萬字含量13字,參照文獻(xiàn)是4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14字﹕13字。(3)“為”字,《尚書》萬字含量22字,參照文獻(xiàn)是127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24字﹕21字。(4)“所”字,《尚書》萬字含量5字,參照文獻(xiàn)是54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5字﹕5字。再補(bǔ)進(jìn)兩個例子:(1)“者”字,《尚書》萬字含量2字,參照文獻(xiàn)是115,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7字﹕1字。(2)“也”字,《尚書》萬字含量0字,參照文獻(xiàn)是170字,古今文篇章之間比例是:0字﹕0字。
完成上述準(zhǔn)確的“字頻作偽”要有一個前提條件,也就是在“作偽”之前預(yù)先確定“偽書”的篇幅。然后才有條件實(shí)施“作偽”過程,還要偽造出“無一字無出處”的效果。實(shí)現(xiàn)這樣的作偽過程和效果幾乎不可能,故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遠(yuǎn)高于前者。從古文篇章“多字組”(100字)萬字含量的平均值略高于今文篇章(35字﹕31字)、“少字組”(8字)萬字含量的平均值略低于今文篇章(31字﹕33字)的情況看,古文篇章的保存質(zhì)量應(yīng)略好于今文篇章。這應(yīng)是古文篇章行文更加流暢一些的主要原因。
我的基本結(jié)論是:“作偽”難度太大,大到不可能的程度。從大量文獻(xiàn)的搜集,到引文、用文的查找;從上百個罕見詞語的查尋采用,到文化、制度方面的理解歸納和融會貫通;從搞清先秦兩漢文獻(xiàn)與今文《尚書》之間字頻不同,到“偽造”過程中的拼湊引文和“字頻勾兌”。如此這般“偽造”的二十五篇不僅沒有明顯綴輯痕跡,且文采尤富于今文。其工程量之大,非一人一世所能及。其道德文章,是黃鐘大呂,絕世風(fēng)華。劉勰所謂“義固為經(jīng),文亦師矣(《文心雕龍·才略》)”。此人是誰?誰能有此移山倒海之力,靈通造化之巧!
在此基礎(chǔ)上,還要將整部《尚書》寫作(包含許多已經(jīng)不是當(dāng)時字體的)“隸古定本”,還要“造”一部今古文同注的《孔傳》。工程量又增加一倍。據(jù)后人研究,“孔傳”解經(jīng)質(zhì)量多有優(yōu)于“鄭注”者。“作偽”動機(jī)是“利益驅(qū)動”,屬投機(jī)行為。但人們一直沒找到因此獲得名利的“作偽”者。這是宋代以來《尚書》“證偽”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之一。“投資”是為“回報”,無些許“回報”的巨大“投資”道理上說不通。假如確有一位“作偽”者,他必是極具才智且勤勉縝密的人。不可能搞不清這個簡單道理。
此外,他是在永嘉之亂前皇家藏書尚有《尚書》古文經(jīng)的情況下實(shí)施“作偽”。──他有病?或是他能預(yù)料日后必有永嘉之亂,且秘府《古文尚書》經(jīng)文必亡于此亂之中。──他是神仙?賈馬鄭王注本他都可以看到,為什么不按照其《書序》所注“亡”、“逸”篇目進(jìn)行“作偽”?為什么不“偽造”十六篇而非要“造”二十五篇?──他到底明白還是糊涂?已知獻(xiàn)書者是梅賾,從“投資”與“回報”上說,如果不是他,工程巨大的投機(jī)行為已經(jīng)變成“義務(wù)勞動”。僅從這一個方面進(jìn)行分析,已經(jīng)足以在邏輯上排除梅賾之外另有作偽者的可能。再從皇甫謐等人對《古文尚書》和《孔傳》的引用,又足以排除梅賾作偽的可能。那么,這部古代文獻(xiàn)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證偽者曾“指控”劉歆、皇甫謐、王肅、鄭沖、梅賾、乃至?xí)x孔安國、孔晁等人是作偽者。從動機(jī)、難度、文獻(xiàn)條件、證據(jù)等方面綜合考察,這些“指控”都屬于查無實(shí)據(jù)的捕風(fēng)捉影。時至今日,人們早已翻遍魏晉間相關(guān)史料,作偽者始終查無實(shí)據(jù)。至少,這些“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煉成獄”的“指控者”都已經(jīng)實(shí)現(xiàn)了各自“炫名”的目的。所謂無利不起早。到底誰是作偽者?——莫須有。
閻氏“魏晉假托”之說還有許多無法成立之處〔51〕。比如,東漢末年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義?過譽(yù)》引用《古文尚書》中《太誓》、《太甲》等篇內(nèi)容;再如,《晉書?荀崧傳》記西晉初期太學(xué)“石經(jīng)古文先儒典訓(xùn)”已有孔氏“章句傳注”之學(xué)。又如,《鄭志》記鄭玄講學(xué)言及《古文尚書·周官》。他對此采用悍然“抹殺”的策略。《疏證》(第六十二):“《鄭志》十一卷,追論康成生平應(yīng)對時人者,今不傳。疑亦多為后人所羼,非本文。何以驗(yàn)之?《周禮?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二語分明是古文《書》。康成及時人安得預(yù)見以相咨問?予謂學(xué)者凡遇此等處,盡從抹殺,不必復(fù)疑焉,以藉口可也。”這叫什么“學(xué)問”!在此有必要強(qiáng)調(diào)指出,在沒有足夠證據(jù)和理由的情況下,絕不可以用自己的主觀見解和推測去否定史料。考據(jù)學(xué)中此種“學(xué)問”很多。存疑為妥。
北京國學(xué)時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xué)網(wǎng)總編室 010.68900123轉(zhuǎn)808
國學(xué)網(wǎng)站,版權(quán)專有;引用轉(zhuǎn)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q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