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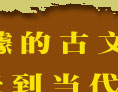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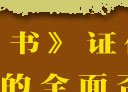

二、《疏證》偽證考略(上)
(2)孔安國蚤卒、家獻
前引孔安國《書大序》提到,他作傳既畢二次獻書,遇巫蠱事未能立于學官。閻氏《疏證》的基本思路是:《書大序》、《孔傳》和“二十五篇”都是魏晉間某人的偽作。如果《書大序》提到的情況屬實,就意味著不存在偽作。這是一個“要害問題”,他必須提出證據給予駁難。他提出“蚤卒”、“家獻”兩個著名“證據”。
《史記·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疏證》(第十七):“司馬遷親與安國游,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倪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后,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于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余歲矣。以二十余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為蚤卒乎?況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何獨于安國而夭之乎?頗不可解。”
《疏證》后文提到(第十七):“向云安國為博士,年二十余。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蚤卒。此安國之壽命也。”閻氏關于孔安國年歲的兩個推算頗有心計,“五十七八”是盡量拉長,“不滿四十”是盡量縮短;由此造成鮮明反差,再以“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俱不謂之蚤卒”作為依據,進而確定縮短的年歲才符合“蚤卒”含義。實際上孔氏子孫在安國前連續四代都是五十七歲,“不過四十、五十”也有盡量縮短之嫌。
閻氏推算巧則巧矣,但并不能排除安國實際年歲在兩個數字之間。漢武帝用人不拘,超遷之事歷歷可數:“卜式試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33〕。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為儒家宗師,安國為孔子嫡孫。因此,漢武帝超遷安國(18~20歲)為博士的可能性極高。《漢書·藝文志》:“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在上述情況下,由于當時《尚書》博士所學只有晁錯傳本及其質量較差的“師說”,又由于“孔壁本”出自孔子舊宅,是孔學之正宗,且其篇數多于前者,文字質量好于前者(后文具體說明),故漢武帝詔令安國“為五十九篇作傳”盡在情理之中。
張湯為廷尉的下限在元狩二年(前121)。上推5年(前 126),安國19歲為博士,次年(前 125)教倪寬。一年后(前 124)倪寬通過考試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又過三年(前 121)武帝以張湯為御史大夫,這一年安國24歲。漢武帝征和元年(前92)巫蠱事起,安國“甫獻《書》而即死”,大約54到55歲。閻氏在《疏證》另一處地方(第一百四)為說明相反問題引《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這里剛好拿來以其矛攻其盾:既然“下壽六十”,那么五十四五歲(甚至按照閻氏所說五十七八歲)為什么不能說“蚤卒”?〔34〕
再者,《史記》述事稱漢武帝為“今皇帝”,僅見于上引《孔子世家》一處。《史記·孝武本紀》裴骃《集解》:“《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后人所定也。”因此,《史記·孔子世家》安國“蚤卒”一條應是后人追記。從述事稱謂“今皇帝”僅見一次(褚少孫也沒有用過)的情況推測,追記的時間,很可能比宣元之間褚少孫補《史記》更晚一些。也就是說,安國“蚤卒”一條極有可能是后人誤記。
《疏證》(第十七):“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游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者也。竊意天漢后,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辯矣。”
《前漢紀·成帝紀》開篇615字(計標點)到《疏證》所引內容:“魯恭王壞孔子宅,……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再向后1070字(計標點)。通計此一千七百余字范圍內,除“孔安國家獻之”一處,“家”字凡26見,除兩處為人名(子家)外,其余24處“家”字含義均與學術有關;這是因為,這一大段文字專講學術源流,即五經、諸子以學名家者的師承傳授情況。比如,“孔子……后世諸子,各……成一家之說。……分為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又如,言五經師說,于《易》施、孟、梁丘之學曰“此三家者”,高氏、費氏曰“此二家者”,于《春秋》曰“公羊家”等。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后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傳《古文尚書》,……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王國維《史記所謂古文說》:“蓋《古文尚書》初出,其本與伏生所傳頗有異同,而尚無章句訓詁。安國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讀而傳之。”〔35〕《漢書?儒林傳》所謂“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指安國為《古文尚書》作章句訓詁,也就是撰寫《孔傳》;所謂“因以起其家”,指“起”其孔氏“《尚書》古文學”的“師說”、“家法”。《前漢紀》“孔安國家獻之”,指安國完成以學名家的訓傳之后的第二次獻書。
針對閻若璩上述說法,毛奇齡《冤詞》已經指出:孔安國第二次獻書因“遭巫蠱,未立于學官”一事,并非安國《書大序》自家所云,而是《漢書》、《前漢紀》等史書多處提到的內容。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即上引史料提到孔安國獻書由于“遭巫蠱”而未能列于學官。《漢書》也提到別的經傳家法未能列于學官的情況,如《藝文志》:“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儒林傳》:“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于學官”。兩種情況明顯不同:后者只說“未得立”、“未嘗立于學官”,而前者則強調了未立的原因。言外之意,如果沒有“遭巫蠱事”將“孔壁本”列于學官本在擬議之中。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講得更加明確:“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前面有決定“施行”,后面才能有“未及施行”。這些都是對安國《書大序》“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的史料呼應。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公司制作
國學網總編室 010.68900123轉808
國學網站,版權專有;引用轉載,注明出處;肆意盜用,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