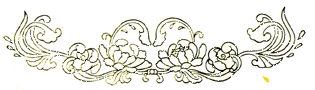| 圍繞 人民大學設立國學院 的消息,國學話題引發了一場坊間熱論,這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國學之事關乎我們這個民族最敏感的文化心理神經。對于人民大學的計劃, 反對者有之 , 支持者也有之 ,這本是健康社會的常態。但是,看到上海學者王曉漁用充滿戲謔的筆調,把倡導儒學的網上帖子斥為“一夜之間刷滿電線桿的老軍醫”廣告,旅美學者薛涌以西方
文明的強勢標準,指責振興國學“體現了國學派對融入世界文化的不甘心”,筆者確實
有些詫異:我們的傳統文化到底背負了多少原罪,值得某些人士如此地鄙夷不屑的字眼冷嘲熱諷?作為學者,對于曾經哺育自己的文明如此虧待,本身可能就是不正常的。
文明新的躍升,孕育于其母體的再度振興
這種不正常恰恰說明了國學的式微已到了何種嚴重的程度。文化是燦爛的,也是脆弱的,它需要精心的照料和培育。中華文化雖是世界文明史上惟一不曾斷代的瑰寶,然而從19世紀至今,它確實面臨著多重的挑戰,但致命的傷害不是來自于外部,而是文明傳承者的自暴自棄,自我淪喪。誠然,在今天看來,傳統文化中有一部分內容難免不合于時,但這正是歷史進步的一個本義,不能因為孩子長高了,就斥責父親變矮了。歷史的第二個本義在于:過去的并不都是落后的。事實反復證明:一種文明新的躍升,往往孕育于其母體的再度振興。中國作為一個正在上升的東方大國,要找準自己的國際和歷史定位,很難離開對自己傳統文化的再度發掘與發揚。
復興國學,是對過去的還債,也是對未來的積財
中國是中華文化的主陣地,兩岸三地在傳承國學方面都有其優長和貢獻,也呈競爭之勢。在香港,由于歷史的原因,國學的一部分血脈得以保存,一些文化倫理與現象仍在當地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在全球華人社會可謂備受青睞,這與作者深厚的國學功底是分不開的。隨著黃霑先生的辭世,具有豐富國學韻味的“黃派詞曲”也成絕唱。但是,香港畢竟彈丸之地,可以成為國學傳播的一個橋頭堡和中轉站,但不可能成為中心地帶。在臺灣,隨著當政者操弄的“去中國化”,國學之色正在消淡。文化是需要地域和人口和國際影響力作支撐的,相比而言,復興國學的重任主要靠大陸,然而同樣由于歷史的原因,傳統文化一度遭到了幾乎是毀滅性的創傷,在中國再次上升的同時復興國學,我們責無旁貸,這既是對過去的還債,也是對未來的積財。
國學研究缺乏一個平臺和論壇
筆者在香港游學數載,對于本港高校開設以國學為主的通識教育很是欣賞,特別是香港城市大學的中國文化中心,常邀全球華人的大方之家于此坐而論道,或激辯,或講學,或切磋,論者相長,聽者受益。其時,筆者初識了很多大陸的國學學者,當時就想:為什么自己在大陸時反倒沒有聽到如此精彩的演講,可能主要的問題就在于:內地缺少類似于“中國文化中心”這樣一個平臺。于此,也希望人民大學的國學院能成為這樣的平臺和論壇。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王曉漁認為,20世紀20年代,北大和清華相繼設立國學研究機構并取得成功,是因為當時條件下,“無論老師還是學生,大都受過完整的國學教育”,因此,今天的人民大學國學院受人力的影響,“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在筆者看來,這絕對不是一條站得住腳的反對理由。正因為國學基礎的脆弱,所以更有必要去想方設法鞏固它。如果今天出于對建設力量的不足而裹足不前,明天的任務將變得更加艱巨甚至不可能。
薛涌認為:“中國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會有生命力”,筆者同意這種判斷。但是,什么是世界文化?難道世界文化就等同于歐美文化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世界文化應當是多種文化的集合體,因此,不能簡單以歐美的一切作標準去衡量中國的一切,即使在技術上可以,甚至在制度上可以,但恰恰在文化層面上絕對不可以。世界文化最基本的立場應當是多元化,衡量一種文化是優是劣,要不要繼續發展,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尺,這乃是文明社會的本義。在這里,容不得一個文明的強權者,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以自我為藍本,先行設定一個框架,對其他的文化方式指手畫腳。如果好好研究一下費孝通先生關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文化觀,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認識這個問題。再者,即使是置身于西方文化的大家庭中,法國、俄羅斯、意大利這些文化重鎮國家都在捍衛自己的特有文化,對此似乎也沒聽說過有多少國民強烈反對。但是,為什么到了中國,自己人做一點自己該做的事情卻總是這么難?
我們不做,誰來做?現在不做,什么時候去做?
復興國學,讓中國傳統文化更好地滋養中國,豐富世界,是我們這一代國民不容放棄的文明使命。套用連戰先生在北大演講時引述里根的名言:“假如我們不做,誰來做?假如現在不做,什么時候做?”畢竟在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我們去做,會比別人做得更好;現在做,會比以后再做,成效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