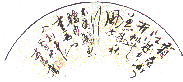特別鐘愛某個(gè)作家的作品后,我往往會(huì)上窮碧落下黃泉,尋尋覓覓,非“一網(wǎng)打盡”不可。于夏志清、唐德剛、洛夫、董橋,可作如是觀。董橋常有少許散文偶爾見于大陸某些報(bào)刊,我也不敢一一放過:《萬象》與《新民晚報(bào)》便是它的載體。
讀過《文字是肉做的》之后,我們不僅見到了比《在語詞的密林里》(陳原)更精彩的董橋,而且對(duì)陳子善亦“懷恨”在心:《英華沉浮錄》還需要選編嗎?為何不能見到原版的董橋?香港畢竟是中國的香港了,為何連我們自己作家的作品還要?jiǎng)h來刪去?遼寧教育出版社真是愛書人的知音。《語文小品錄》就是《英華沉浮錄》的全貌,竟然出到第10冊(cè)了。《文字是肉做的》僅僅是1~3冊(cè)的選本,被刪掉的那些篇章,很有些值得大陸知識(shí)分子反思的精品。
余光中有篇專論散文篇名如何命名的批評(píng)文字,算是我讀到的當(dāng)代散文家中最好的一篇;而他自己也是追求散文篇名之精彩之有立體感而欲超越前人的實(shí)踐者。董橋,也是一位命名的高手。依然秉持特有的風(fēng)格——在馬克思的胡須叢中和胡須叢外——他為文章構(gòu)思篇名,仍是精彩紛呈、獨(dú)特飄逸,書名亦然。董橋云:“寫作構(gòu)想題目是最好玩也最痛苦的斗爭。”請(qǐng)看:香港中文不是葡萄酒、新聞是歷史的初稿、留住文字的綠意、天氣是文字的顏色、為紅袖文化招魂、人道是傷春悲秋不長進(jìn)、給自己的筆進(jìn)補(bǔ)。這些是篇名,也是書名,真讓人賞心悅目啊。胡適于1942年夏天被蔣介石免去駐美大使而做寓公時(shí),常常翻看《人民日?qǐng)?bào)》,喜好給昔日學(xué)生毛潤之等“平作文”、“看考卷”。然而,其中之批語如何?局外人如吾輩者,僅能在唐德剛《胡適雜憶》中探得消息,而讀不到老師之眉批矣。
《語文小品錄》正是董橋給那些詞匯不足、文章貧血、句法笨拙、陰陽不調(diào)之作的點(diǎn)評(píng),也是給幾代文人墨客之大作的一些眉批,——是煉石補(bǔ)天的真跡,是文字煉到高妙處的真知灼見,也是中國知識(shí)分子的良知。感嘆迷失在曠野中的吳晗(余英時(shí)對(duì)吳晗也有微詞),為活活給塵垢和毒藥埋葬的吳宓控訴(為此我專程跑到吳宓墓而祭拜一番,算聊盡陜?nèi)酥椋衣锻袪査固┑牧懿。薷拿珴欀畷诺牟蛔阒帲u(píng)《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個(gè)別例句,欣賞老舍買來吳祖光散失的藏畫而歸還原主的磊落胸懷,展示胡適的英文的流暢、美麗;介紹于右任的卷卷家書,贊美為香港回歸立下汗馬功勞的張幼云的傳譯,敬佩林太乙中英文的非凡功底,思念成都玉林街的龔明德……。每一冊(cè)五六萬字,每一篇千字以內(nèi),幾乎篇篇精彩,很是耐讀。
電話、電視、電腦的發(fā)達(dá)泛濫,把匆忙的人群逼上一條艱險(xiǎn)而繁忙的人生之路。但是,我寧愿放棄浮躁,而與書為伴。《語文小品錄》是滾滾紅塵中我讀到的非常清醒而冷靜的文字,是漫漫冬夜里溫馨的燈盞。最讓人低回呻吟而冥思苦想的是:為何身在文革之外的董橋,卻寫出了讓大陸知識(shí)分子感到慚愧而反思文革的大作!
當(dāng)然,董橋也常常在引用材料上,不夠謹(jǐn)慎,也時(shí)時(shí)靠海內(nèi)外的讀者幫忙,修訂不足之處。天天寫專欄文章,稍有閃失,也在情理之中。請(qǐng)看《語文小品錄(7)》《為紅袖文化招魂》第90頁《文字輪回六道中》一文:
早年讀過一首《圈兒詞》,覺得好玩,背得幾句,忘了全首。昨天看到臺(tái)灣的黃友玲寫出來了,趕緊剪存。說的是清朝有個(gè)婦人思念丈夫,又不識(shí)字,就在信紙上畫了大大小小或單或雙或破或圓的圈圈,寄去給遠(yuǎn)方的丈夫。一位秀才偶然看到這封信,感動(dòng)之余,揣摩婦人心意,寫出這首《圈兒詞》:“相思欲寄無從寄,畫個(gè)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里。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tuán)圓,破圓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黃友玲說這首詞“文詞淺白,情感真摯,數(shù)十字便把這思婦的心情描述得淋漓盡致。”
董橋在該文中又稱贊道:“這首《圈兒詞》如果出自那個(gè)婦人的手筆,也許就肉麻了。幸好她只會(huì)畫圈圈,也湊巧那個(gè)秀才多事,這十幾個(gè)字終于傳世了。圈圈代信當(dāng)然比《愛眉小札》動(dòng)人,等于棄掉了文字的矯情。秀才將之還原為文字,既證明圈圈之真諦,也證明文字功能之不死。”
可是,我在清人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二“圈兒信”中卻見到另一版本:
有妓致書于所歡,開緘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shù)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末畫無數(shù)圈。有好事者題一詞于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個(gè)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里。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tuán)員,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上海古籍出版社點(diǎn)校本第64頁)
我治姓名學(xué),常常愛翻看一些明清筆記野史:同一材料,總會(huì)有不同的說法和版本;一般來說微殊而有之,迥異則難遇。這本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假如《圈兒詞》乃“妓致書于所歡”與“好事者”所為,其格調(diào)總不至于超過《愛眉小札》吧?我倒不會(huì)學(xué)士大夫梁紹壬的忍不住笑,而我起碼知道,董小宛、柳如是固然也能寫出《夢(mèng)憶》、《懷人》的情詩來,但較之李商隱的《無題》(相見時(shí)難)、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陸游的《釵頭鳳》(紅酥手),當(dāng)不在一個(gè)境界里,即使與柳永的《雨霖鈴》(寒蟬凄切)、《八聲甘州》(對(duì)瀟瀟暮雨)相比,孰伯孰仲,讀者心中自明。
當(dāng)然,還是董橋說的妙不可言:“文章是剪裁史料縫制而成的繡花被子,各人所取角度與觀點(diǎn)不同,可正可負(fù),可褒可貶。”(見《托爾斯泰的淋病》)而錢鍾書則更老辣:假如你吃了雞蛋覺得不錯(cuò),何必認(rèn)識(shí)那下蛋的母雞呢?
總之,我總覺得:年輕時(shí)不讀陳獨(dú)秀、李敖,無論讀與寫,總會(huì)缺少一種激情;中年而不讀董橋,不是腦子太忙、精子太閑,就是精子太忙而腦子太閑——永遠(yuǎn)培養(yǎng)不出溫文爾雅的書香情懷。董橋當(dāng)然是永遠(yuǎn)的下午茶、夜闌人靜的枕邊書。
《語文小品錄》,董橋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