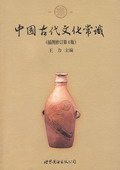
《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第4次修訂版)
作 者:王力 著
出 版 社: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出版時間:2008年1月第2版
書 號:978-7-5062-8689-3
定 價:¥25.00 元
第一章 天文
出土這塊彩錦的墓葬是一座男女合葬墓,時間為東漢末到魏晉。陪葬品中有一件陶器還帶“王”字題記。這件彩錦織物出土時位于弓的旁邊,說明它在使用弓的時候是系在射手的前臂上的。錦邊緣縫的織物是絹。這塊彩錦是五重平紋經錦(使用了藍、綠、黃、紅和白這五種顏色的經線)。錦上織有日月、云朵、孔雀、仙鶴、辟邪和虎的紋樣以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
這里的“五星”,是先秦所謂的太白、歲星、辰星、熒惑和鎮星。在秦漢以后,由于五行說的普及,它們又被稱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
所謂“中國”,是星占學分野概念里的“中國”,泛指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而“中國”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國”。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古代星占學上很常見的占辭。《史記·天官書》上說:“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在《漢書》、《晉書》、《隋書》、《新唐書》天文志以及《開元占經》里都能見到類似的記載。
“五星積于東方”和“五星出東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時期內,在日出前同時出現在東方。這種天象非常罕見,所以引起古人格外的好奇與重視,把這種天象附會上某種“天意”。比如《文獻通考》上就有“周將伐殷,五星聚房”之說。
五星聚合一般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出現一次。中國上一次出現聚合(間距<30°)的時間是公元1921年。下一次出現五星聚合的時間則是公元2040年了。
因為這件彩錦護膊出土時正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騰飛壯大的時期,而新中國的國旗又是五星紅旗,所以人們在不具備相應古代文化知識情況下,從這件護膊上讀出的是直白的現代字面意義。這件護膊被定為一級甲等并受到格外的珍視當然也就很好理解。
在上古時代,人們把自然看得很神秘,認為整個宇宙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主宰,就是帝或上帝。在上古文獻里,天和帝常常成為同義詞。古人又認為各種自然現象都有它的主持者,人們把它們人格化了,并賦予一定的名字,例如風師謂之飛廉,雨師謂之荓翳(屏翳。葬,讀ping;翳,讀yi),云師謂之豐隆,13御謂之羲(xi)和,月御謂之望舒(這里是舉例性質,見《廣雅·釋天》),等等,就是這種觀念的反映。這些帶有神話色彩的名字,為古代作家所沿用,成了古典詩歌辭賦中的辭藻,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農耕生活的國家之一,農業生產要求有準確的農事季節,所以古人觀測天象非常精勤,這就促進了古代天文知識的發展。根據現有可信的史料來看,殷商時代的甲骨刻辭早就有了某些星名和13食、月食的記載,《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國語》、《爾雅》等書有許多關于星宿的敘述和豐富的天象記錄,《史記》有《天官書》,《漢書》有《天文志》。我們可以說遠在漢代我國的天文知識就已經相當豐富了。
古人的天文知識也相當普及。明末清初的學者顧炎武說: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戶”,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辰”,兒童之謠也。后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見《日知錄》卷三十“天文”條。“七月流火”見《詩經·豳風·七月》,“三星在戶”見《詩經·唐風·綢繆》,“月離于畢”見《詩經·小雅·漸漸之石》,“龍尾伏辰”見《左傳·僖公五年》。)
我們現在學習古代漢語當然不是系統學習我國古代的天文學,但是了解古書中一些常見的天文基本概念,對于提高閱讀古書能力無疑是有幫助的。現在就七政、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分別加以敘述。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合起來稱為七政或七曜(yao)。金木水火土五星是古人實際觀測到的五個行星,它們又合起來稱為五緯。
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為它光色銀白,亮度特強。《詩經》“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見《詩經·鄭風·女曰雞鳴》),“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見《詩經·陳風·東門之楊》),都是指金星說的。金星黎明見于東方叫啟明,黃昏見于西方叫長庚,所以《詩經》說“東有啟明,西有長庚”(見《詩經·小雅·大東》)。木星古名歲星,逕(jing)稱為歲。古人認為歲星十二年繞天一周,每年行經一個特定的星空區域,并據以紀年(下文談到十二次和紀年法時還要回到這一點上來)。水星一名辰星,火星古名熒惑,土星古名鎮星或填星。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談到天象時所說的水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營室,即室宿,主要是飛馬座的α、β兩星),《左傳·莊公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就是一個例子。所說的火也并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即心宿,特指心宿二,即天蝎座的α星。《史記·天官書》所說的火,才是指火星(熒惑)),《詩經》“七月流火”,就是一個例子。
古人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是以恒星為背景的,這是因為古人覺得恒星相互間的位置恒久不變,可以利用它們做標志來說明日月五星運行所到的位置。經過長期的觀測,古人先后選擇了黃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個星宿作為“坐標”,稱為二十八宿。黃道是古人想像的太陽周年運行的軌道。地球沿著自己的軌道圍繞太陽公轉,從地球軌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陽,則太陽在天球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相同。這種視位置的移動叫做太陽的視運動,太陽周年視運動的軌跡就是黃道。這里所說的赤道不是指地球赤道,而是天球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星宿這個概念不是指一顆一顆的星星,而是表示鄰近的若干個星的集合。古人把比較靠近的若干個星假想地聯系起來,給以一個特殊的名稱如畢參箕斗等等,后世又名星官。二十八宿指的是:
東方蒼龍七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 斗牛女虛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 奎婁胃昴(mao)畢觜(zi)參
南方朱雀七宿 井鬼柳星張翼軫(zhen)
東方蒼龍、北方玄武(龜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這是古人把每一方的七宿聯系起來想象成的四種動物形象,叫做四象。
以東方蒼龍為例,從角宿到箕宿看成為一條龍,角像龍角,氐房像龍身,尾宿即龍尾。再以南方朱雀為例,從井宿到軫宿看成為一只鳥,柳為鳥嘴,星為鳥頸,張為嗉(su),翼為羽翮(he)。這和外國古代把某些星座想象成為某些動物的形象(如大熊、獅子、天蝎等)很相類似。
上文說過,古人以恒星為背景來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而二十八宿都是恒星。了解到這一點,那么古書上所說的“月離于畢”、“熒惑守心”、“太白食昴”這一類關于天象的話就不難懂了。(其中《尚書·洪范》偽孔傳:“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熒惑守心”見《論衡·變虛》篇;“太白食昴”見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月離于畢”意思是月亮附麗于畢宿(離,麗也);“熒惑守心”是說火星居于心宿;“太白食昴”是說金星遮蔽住昴宿。如此而已。蘇軾在《前赤壁賦》里寫道:“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也是用的二十八宿坐標法。
二十八宿不僅是觀測日月五星位置的坐標,其中有些星宿還是古人測定歲時季節的觀測對象。例如在上古時代,人們認為初昏時參宿在正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等等。這是就當時的天象說的。《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五月初昏大火中。”
古人對于二十八宿是很熟悉的,有些星宿由于星象特殊,引人注目,成了古典詩歌描述的對象。《詩經》“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yi)酒漿”(見《詩經·小雅·大東》),這是指箕宿和斗宿說的。箕斗二宿同出現于南方天空時,箕宿在南,斗宿在北。箕宿四星聯系起來想象成為簸箕形,斗宿六星聯系起來想象成為古代舀酒的斗形。《詩經》“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則是指參宿而言(此從毛傳),因為參宿有耀目的三星連成一線。至于樂府詩里所說的“青龍對道隅”(見《隴西行》),道指黃道,青龍則指整個蒼龍七宿了。有的星宿,伴隨著動人的神話故事,成為后世作家沿用的典故。膾炙人口的牛郎織女故事不必敘述。(但是織女不是指北方玄武的女宿,而是指天琴座的α星;牛郎也不是指北方玄武的牛宿,而是指天鷹座的僅星,牛郎所牽的牛才是牛宿。)二十八宿中的參心二宿的傳說也是常被后人當作典故引用的。《左傳·昭公元年》說: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日閼伯,季日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zang),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主祀大火),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即心宿);遷實沈于大夏(晉陽),主參(主祀參星),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即參宿)。
因此后世把兄弟不和睦比喻為參辰或參商。又因為參宿居于西方,心宿居于東方,出沒兩不相見,所以后世把親朋久別不能重逢也比喻為參辰或參商。杜甫《贈衛八處士》所說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就是這個意思。
隨著天文知識的發展,出現了星空分區的觀念。古人以上述的角亢氐房心尾箕等二十八個星宿為主體,把黃道赤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照由西向東的方向分為二十八個不等份。在這個意義上說,二十八宿就意味著二十八個不等份的星空區域了。
古代對星空的分區,除二十八宿外,還有所謂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黃河流域常見的北天上空,以北極星為標準,集合周圍其他各星,合為一區,名日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張翼軫以北的星區是太微垣;在房心尾箕斗以北的星區是天市垣,這里不一一細說。
現在說一說北斗。北斗是由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七星組成的,古人把這七星聯系起來想像成為古代舀酒的斗形。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組成為斗身,古曰魁;玉衡、開陽、搖光組成為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屬于大熊座。
古人很重視北斗,因為可以利用它來辨方向,定季節。把天璇、天樞連成直線并延長約五倍的距離,就可以找到北極星,而北極星是北方的標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節和夜晚不同的時間,出現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們看起來它在圍繞著北極星轉動,所以古人又根據初昏時斗柄所指的方向來決定季節:斗柄指東,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現在說到十二次。
古人為了說明日月五星的運行和節氣的變換,把黃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東的方向分為星紀、玄枵(xiao)等十二個等份,叫做十二次。每次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為標志,例如星紀有斗牛兩宿,玄枵有女虛危三宿,余皆仿此。但是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的廣狹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訖界限不能和宿與宿的分界一致,換句話說,有些宿是跨屬于相鄰的兩個次的。下表就說明了這種情況(此表是根據《漢書·律歷志》作的,各次的名稱、寫法和順序都根據《漢書·律歷志》)。
我國古代創立的十二次主要有兩種用途:第一,用來指示一年四季太陽所在的位置,以說明節氣的變換,例如說太陽在星紀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等等。第二,用來說明歲星每年運行所到的位置,并據以紀年,例如說某年“歲在星紀”,次年“歲在玄枵”,等等。這兩點,后面談到歷法時還要討論。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上述十二次的名稱大都和各自所屬的星宿有關。例如大火,這里是次名,但在古代同時又是所屬心宿的名稱。又如鶉首、鶉火、鶉尾,其所以名鶉,顯然和南方朱雀的星象有關,南方朱雀七宿正分屬于這三次。《左傳·僖公五年》“鶉火中”,孔疏說“鶉火之次正中于南方”,又說“鶉火星者謂柳星張也”,可以為證。
下面談談分野。
《史記·天官書》說“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可見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聯系起來看的。在春秋戰國時代,人們根據地上的區域來劃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別指配于地上的州國,使它們互相對應,說某星是某國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國的分野;也有反過來說某地是某某星宿的分野的。例如《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野也。”這種看法,便是所謂分野的觀念。
古人所以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為了觀察所謂“機(ji)祥”的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國的吉兇。例如《論衡·變虛篇》講到熒惑守心的時候說:“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顯而易見,這是一種迷信。但是古人對于星宿分野的具體分配既然有了一種傳統的了解,那么古典作家作品在寫到某個地區時連帶寫到和這個地區相配的星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庾(yu)信《哀江南賦》說“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王勃《滕王閣序》說“星分翼軫”,李白《蜀道難》說“捫(men)參歷井”,就是在分野的意義上提到這些星宿的。
最后應該指出的是,古人的天文知識雖然已經相當豐富,但是由于科學水平和歷史條件的限制,古代的天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宗教迷信的占星術相聯系的。古人對于某些異乎尋常的天象還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于是在崇敬天帝的思想基礎上,把天象的變化和人間的禍福聯系起來,認為天象的變化預示著人事的吉兇。例如日食,被認為對最高統治者不利,所以《左傳·昭公十七年》說:“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殺牲盛饌(zhuan)〕,伐鼓于社。”《禮記·昏義》也說:“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這是把日食看成是上天對最高統治者的警告。又如彗星(一名孛星,欃槍)的出現,被認為是兵災的兇象,所以史書上常有記載。甚至行星運行的情況也被認為是吉兇的預兆。例如歲星正常運行到某某星宿,則地上與之相配的州國就五谷昌盛,而熒惑運行到這一星宿,這個國家就要發生種種禍殃,等等。占星家還認為某某星主水旱,某某星主饑饉,某某星主疾疫,某某星主盜賊,注意它們的隱現出沒和光色的變化而加以占驗。這些就不一一敘述了。
占星無疑是迷信,占星術后來被統治階級所利用,成了麻醉人民的工具,我們閱讀古書,對此應該有所了解。
2-9《佛說盂蘭盆經》、《父母恩重難報經》、《瑜伽焰口》金陵刻經處現代印本
中元節是中國人非常重要的祭祀去世親人的節日,意義不在清明節之下。中元節的傳統在20世紀50年代曾一度中斷,不過近年在民間又自發地得到了很大的恢復。
中元節又叫盂蘭盆節。盂蘭盆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譯,這個詞原意為“從苦難中拯救”,中國舊譯“解倒懸”。盂蘭盆節的來歷和目犍連(也就是中國民間目連戲的男主角目連)救母的故事有關。
這個故事就記錄在《佛說盂蘭盆經》里:目犍連得了六神通以后,用法力觀看世界,發現自己已經去世的母親墮入餓鬼道中。目犍連送給母親飯食,可是飯一遞到母親手上就化成火炭。
目犍連哭著求佛陀解救。佛陀說,你母親生前(喜歡吃魚籽,所以殺生數量太大)罪孽深重,想要解救她,憑你一人之力無法完成,憑我一人之力也無法完成。我們只有憑借佛、法、僧這“三寶”的力量,才能解救她。佛陀告訴目犍連,每年七月十五日,是佛歡喜日,我們都要集結佛法僧三寶的力量,超度我們的七世父母。
這個故事的內涵,其實還遠比它表面上看要來得深刻。最初的佛教是小乘佛教(梵文Henayana),也就是只管修行超度自己,不理世事,只能裝一個人的“小車”。而盂蘭盆經講的是大乘佛教(梵文Mahayana),也就是除了自度之外,還要“度人”(超度別人)的,能裝很多人的“大車”。(梵文中yana意為“車乘”,hena是小,maha是大,henayana就是“小乘”,mahayana就是“大乘”。)實際上,佛教界內的人大多認為盂蘭盆的故事講的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轉化的原因。為了超度自己故去的親人以及拯救孤魂野鬼,小乘佛教就發展成為需要結合佛法僧三寶力量的大乘佛教。(在中亞發源、北傳到中國的佛教到唐代以前還小乘、大乘并存。唐代中國流行的就基本上全是大乘佛教了。當然,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轉化的真正原因和過程遠比目連救母這個故事本身復雜得多。限于篇幅這里不介紹。)
在每年陰歷七月十五,也就民間俗稱的“鬼節”,中國人都會給家里去世的親人燒紙錢。佛教寺廟里也會舉辦法事活動,超度亡靈,給餓鬼施食,同時祝年長者健康長壽。這種法會活動,就叫做“放焰口”。
“放焰口”原本是佛教密宗的儀軌,現在卻廣為北傳大乘佛教寺廟采用。按照《瑜珈焰口》的說法,餓鬼頸如細針,不能進食。做法事的法師結合佛、法、僧三寶的力量,用密咒使餓鬼喉嚨變粗。法師們向空中撒米,使得餓鬼能吃上一頓飽飯。這里的“焰口”,就是頸如細針、面上噴火的餓鬼的名字。講放焰口起源的故事的佛經是《救撥焰口惡鬼陀羅尼經》,故事內容與《佛說盂蘭盆經》有相似性。
4-2中國黃河流域近3500年來年平均氣溫變化曲線圖(據王錚、王會昌)
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希多尼(Posidonius,約公元前135-約公元前50年)最早提出了氣候對于人的性格有重大影響的理論。這種“人種的地理”概念為現代人類學所繼承。大量人類學者認為,氣候對于每個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性的形成有決定性作用,氣候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近3500年來中國歷史上曾經歷過三個氣候溫暖濕潤時期和三次大規模的變冷。中國史學界對于這些宏觀氣候變化一直比較缺乏概念,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有蒙文通指出先秦時期黃河流域的氣候遠比現在溫暖。但這個粗略的論斷也僅局限于為史學專家中的極少數人所知。
大量自然科學、考古學、歷史文獻證據表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即武王克商,商周政權交替時期),中國處在“仰韶暖期”,與當時全球性的“大西洋氣候期”的相對應。黃河流域當時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大約3℃。那時的夏天冬天溫差小,雨水豐沛,草木茂盛,和現在長江流域的亞熱帶氣候相當。而當時長江流域氣候則與現在珠江流域氣候相當,為熱帶雨林所覆蓋。
在氣候溫暖的時候,中國北方的游牧政權與中原農耕世界和平共處。一旦氣候變冷,游牧民族的放牧業出現障礙,為了不被餓死就必須南遷,與中原政權爭奪南方的草場,戰亂也由此而來。每次氣候變冷,北方游牧民族政權南部疆域的版圖都必須擴大。如果不能擴大,這些游牧民族政權就會滅亡。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變冷發生在西周。《竹書紀年》中有公元前903年長江、漢江結冰的記載。冷到長江、漢江會在冬天結冰,在今天是人們難以想象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隨處可見“中國”(詳見《天文》一章關于“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彩錦護膊的注釋)與夷狄戎(róng)羌(qiāng)玁(yán)狁(yǔn)交戰的紀錄。這些“侵略者”大多是北方游牧民族。
第二個寒冷期對應的是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當時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2℃~4℃。這個時代出現的是“五胡亂華”之后的十六國割據局面。
第三個冷期發生在宋元之間。經歷長時段的氣候變冷、草木凋零、糧食減產和連年瘟疫與戰爭,中國的政權達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在公元1234年這個臨界點,和宋代趙家王朝征戰百年的游牧民族大金國瞬間崩潰,被新興壯大的蒙古人政權消滅;而南宋的趙家王朝,也不過是在王朝覆滅前茍延殘喘。蒙古人建立的牧者王朝,隨后為中國建立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疆域版圖。
由此很多看上去奇怪的事情我們也就好理解了。周代《詩經》里不斷歌誦黃河流域各諸候國的水稻和桑田,而《禹貢》又說,“斷發紋身”的越人(揚州人)“島夷卉服”。稻子需要種在水田里,雖然今天黃河流域沒多少水田,更適合干地種麥子,但西周情況則不然;因為當時的長江流域實在太熱,越人才光著膀子穿得那么少。(卉服,指用長滿樹葉的樹枝做的“衣服”。今天斯里蘭卡的Wedda土著人迎接客人時仍然穿著“卉服”。)同樣,中國的“隋唐晚期”對應于歐洲的“中世紀暖期”。那時的氣候溫暖,才有了驚人的農業豐收、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太平盛世。
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黃河流域中國文明起源的仰韶、龍山文化遺址現在往往是生態環境極為惡劣的不毛之地。這給現代人常帶來不可思議的荒謬感。其實,一直到唐代以前,現今的河西走廊戈壁灘都還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植被的大規模破壞、生態的惡化,一部分是因為歷代中國人過度的砍伐開墾,另一部分原因就是三千多年來經歷的三次大規模氣候變冷,導致了地表植被消亡的土地荒漠化。
近世全球氣候變暖,但這個變暖的升溫幅度同中國3500年來的三次大規模變冷降溫幅度相比,根本是小巫見大巫。從另一個角度說,人的命運雖然同這個星球緊密綁在一起,要滅亡卻也沒那么容易。
7-1清代刊本《百家姓》
姓和氏都是宗族血親關系的代號。姓和氏的概念及來源本身的問題也非常深奧復雜。從古代文獻結合甲骨文、金文的情況來看,姓,原本是指母親一系的血緣關系;氏,原本指的是父系的血緣。我們今天概念的“姓”,實際上是先秦時代的氏,是父系血緣宗族符號。而先秦時代原本的“姓”的概念,在戰國時逐漸淡薄,到了西漢已經消失得非常徹底,以致于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有時竟然把“姓”、“氏”相混淆。先秦所謂“同姓不婚”的原則,原來也是指母方同血統者不能結婚。
非常有趣的一點是,漢代以后“姓”發展成父系血緣的代號,而“氏”除了指父系血緣之外(比如“山東丁氏旺族”“江西劉氏宗族”)居然常被用來指母系血緣。比如劉姓人家的女兒嫁到陳家(舊時女子大多沒有學名),就被稱做劉氏或者陳劉氏。“姓”和“氏”的涵意和指代關系的這種交換至今未見到任何合格的學術解釋(這個問題也極少為人所知)。姓氏問題本身也被有的學者認為是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化的證據,但是這種立論未必嚴謹。弗洛伊德寫的《摩西與一神教》和《圖騰與禁忌》兩書所闡述的問題與此相類似,或許能提供有益的啟發。
7-3b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2007年演出昆曲《孟姜女》的宣傳廣告
孟姜女廟原建于宋代。現存的孟姜女廟據說是“明萬歷年間的建筑”,但旅游局對孟姜女廟的修整附會鄙俗不堪,讓觀者驚恐錯愕。
孟姜女廟前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對聯: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長長長長長長長消。這副對聯的句讀(dòu)有十多種,最常見的斷句讀法是: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朝,讀zhāo,意思是早晨);浮云漲,常常漲,常漲常消。
孟姜女姓姜而不是姓孟。孟姜女,意思是姜家大女兒。先秦青銅器銘文中體現出來的姜姓,在周代是勢力非常大的貴族。《太平御覽》里甚至說,戰敗給黃帝的蚩尤,也是姜姓。“孟姜女哭倒長城八百里”傳說中的孟姜女,并不是清代話本中底層平民萬喜良的貧賤妻子,而是《春秋左傳》里齊國大將杞梁的貴族妻子。這個故事原始面貌只是貴族姜姓家一個女人的丈夫戰死,小寡婦出來向齊王要求提高追悼會的規格。故事流傳到唐代才定型成孟姜女哭倒秦長城。
孟姜女故事的原始發生地點在今山東省。孟姜女廟在今河北省的最北端,而遙遠的臺灣也在2007年新排出昆曲《孟姜女》。姜姓貴族的力量,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溶進了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成為中國“哭功”、“哭戲”的代表性符號。在今天的山東淄博,白事活動中仍然可以見到中老年婦女用平時唱孟姜女的傳統曲調來哭喪,令外地人驚愕不已。
8-1a酉(yǒu)瓶 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半坡類型) 距今約6000年 高46厘米
1958年陜西寶雞北首嶺出土這種瓶子過去學界通常定名為“小口尖底彩陶瓶”,用作汲水器(日常生活中取水用的瓶子)。學界認為瓶子之所以做成這個怪形狀,是空瓶置入井中后它會自動平倒下,瓶口落到水面,方便井水灌注進瓶里;等瓶中的水灌滿,瓶子則會自動恢復成豎直狀態,利于從井中提出。瓶子的尖底還有利于它的放置:尖底可以很方便地插在松軟的土中。
問題在于,新石器時代的人基本上還不會打“井”,他們主要是從河里汲水,而這種瓶子從河里汲水幾乎沒有任何優越性;當時日常住所的泥土地面在生活中被往返地踩來踩去,會導致“地面固化”。尖底瓶在固化的地面上豎直放置穩當的困難程度顯而易見:泥土“松軟”到可以插得住這種瓶子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學界將它解釋為日常生活取水的汲水器并不合理。
這種小口尖底瓶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看上去很多,但絕大多數都是殘碎的,能選出典型完整的標本很少。小口尖底瓶的出土數量和分布等性質以及器物本身的形狀、結構特性說明它們并不是大量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器,而更像是一種和宗教或祭祀有關的器物。蘇秉琦認為,小口尖底瓶具有“神器”的性質,為神職人員所專用。
其實這個瓶子應該被定名為“酉瓶”。“酉”在甲骨文中寫為“■”或“■”,它象征一種小口尖底的酒器的形狀,引申有“酒”的意思。《說文》也說:“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酎(zhòu),《說文》上說:“酎,三重醇酒也。”酎是用糖度高而酒精度低的醴(lǐ)代替水,加到米和酒曲中制成的重釀酒。重釀酒的酒精濃度最高能達到10%。《說文》對于“酉”字的解釋是說:酉就是八月成熟的黃黍做成的重釀酒。酉是“酒”和“尊”的本字。后來“酉”被借用去表示天干地支,為了區別,人們在“酉”字旁邊加上“水”的偏旁,這就是“酒”,而表示盛酒器則是在“酉”旁邊加上了一雙捧著酒的手“■”,這就是“尊”。商周青銅禮器里非常重要的一類就是作為盛酒器的尊。
仰韶文化的酉瓶是被專門用來裝酒的“神器”。
9-1湖南湘潭韶山毛氏宗祠
毛氏宗祠是韶山毛氏家族的總祠堂。毛澤東即出于韶山毛氏。祠堂始建于公元1758年。1968年人民政府對毛氏宗祠進行過全面大修,并在該年年底對外開放。
宗法,即祖宗之法,是以血緣和家庭為紐帶建起來的等級制度。在1949年以前的三千年中,宗法制度的力量一直都是非常強大的。中國人在誰是自己祖宗的問題上從來都很嚴肅。人們使用“不肖子孫”這個詞時的心態,要么是高度的內疚,要么是最刻毒的指責。
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漫長而艱險,如同船過三峽。這個進程已經持續了一百五十多年,到今天仍然沒有結束。假如我們把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危機和災難比作從天而落的巨石,那么國家的各層力量就是一層層用來托擋巨石的網,使得巨石下的人不會全被砸死。而這些網中最靠下面同時也是最有力量的一層,就是宗法。
在宗法制度的時代,人民是“高度自治的”。常見的民事糾紛(包括小的經濟糾紛和刑事案件)都是請“三老”(同族的三位長者)裁斷。三老不能解決,才會開祠堂。鬧到要開祠堂,通常都是非常大的事了。祠堂里族長和長輩甚至有權決定當事人的生死。經過宗族力量過濾后仍需要上升到官府手里的案子,是不多的。宗法制度和“三百文官治天下”的國家機器,在功能上協同互補。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抗日戰爭淪陷區的中國民眾,在徹底沒有政府真正管理的十年中(國民黨跑了,日本人又管不過來)如何得以生活尚有一定秩序。
宗法制度在1949年以后訇然中塌,被摧毀得幾乎不留痕跡。這讓我們既欣喜又惋惜。宗法制的解體帶來了社會某些方面的進步,但宗法體系所具有的維護國計民生的力量,也永遠地消散了。
9-3《南山橋楊氏族譜》 1919年垂裕堂木活字本 無錫市圖書館藏
喪服制度出自《儀禮》。表面上看,喪服制度是在說什么樣的親戚死了應該穿相應的什么孝服的無聊事,而實際上,喪服制度的核心仍是宗法思想。喪服涵蓋范圍之外,即“出了五服”(“五服”之外),就算遠親。民間有說法“遠親不如近鄰”,意思是說出了宗族五服之外的親戚不如鄰居。但五服之內的近親,再怎么不堪,也比近鄰來得有用。宗法力量之強大,由此可見一斑。
喪服制度中,還有很多怪現象,比如“姨”服重于“舅”服(即媽媽的姐妹的地位居然比媽媽的兄弟高一級),“叔嫂無服”。(我們說“長嫂如母”,如果父母去世早,大嫂就相當于母親,負責把小叔拉扯大,小叔也要把大嫂當母親看待。但是即便如此,小叔子和嫂子之間卻沒有喪服關系。)這些現象的真實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文明。
又比如,《儀禮》中“姑”、“舅”都是多意稱謂。“姑”可以用來指丈夫的姐妹,同時又可以指丈夫的媽媽(即女子的婆婆);“舅”可以用來指母親的兄弟,同時又可以指丈夫的爸爸(即女子的公公)。這背后的原因,絕不是庸俗地套用“親親尊尊”言論所能解釋的。雖然有人認為這是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轉化的證據,或者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轉化的證據,但這些觀點都論證粗疏,難以憑信。
記錄宗法制度最重要的載體就是“家譜”。“自家不打自家人”、“家丑不可外揚”都局限于家族、宗族內部。家譜被焚毀,宗法制度也很容易就灰飛煙滅。經歷近世二十載的劫火,幸存到今天的族譜,比之一個世紀之前的狀況,已經是寥若晨星了。
12-2豬面鳥首彩陶壺摹本
豬面鳥首彩陶壺高20.8厘米,1981年出土于甘肅秦安王家陰洼。陶壺制作使用的時代是新石器時代,屬于半坡晚期文化類型。
摹本為同一彩陶壺的正面主視圖以及左視圖。主視圖中的墨線非常形象地表現了豬的臉。而且圖中的豬沒有獠牙,說明這是已經馴化的家豬而不是野豬。左視圖中圓圈和圓圈中的點表示從圓錐頂點向下俯視看到的圓錐投影,它表現的是鳥的嘴。
古代常用豬代表財富和生育,代表女性;鳥則代表權力,代表男性。
在游牧民族的畜牧經濟中,豬是難養的動物(豬不像牛、羊、狗那樣適合游牧遷徙)。從這一點講,很多講肉食的字,從“牛”或從“羊”而極少從“豕”是很好理解的。
中原方國在距今八千年前完成了游牧狩獵經濟向(定居的)種植農業經濟的轉化,但是和肉食有關的字還保留了較多游牧狩獵生活的特征,即牛、羊做偏旁居多。隨著種植業的發展和豬的馴化,很多和豬有關的字產生出來,比如“家”(房子底下有豬。豕,讀shǐ,意思就是豬)、“圂”(圂,讀hùn,意思是廁所,即廁所通豬圈。現代中國南方和北方農村仍然能見到人的廁所就是豬圈、豬養在人的廁所里的實例。)。
另外,我們常說的“腥”、“臊”二字也和豬有關。《周禮?天官冢宰》上說腥、臊不能食。《說文》上解釋說,所謂“腥”,并不是肉聞上去的味道,而是“肉中的星星”,指豬肉中有像米粒的星星點點的肉息(長有寄生蟲豬肉絳蟲的“米星豬”);所謂“臊”,是豬身上油脂發臭。對于屠宰前檢疫和食品安全的問題,周代的人只怕比現在還控制得好一些。
14-1司母戊鼎 商代晚期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9厘米1939年河南安陽武官村出土
司母戊鼎重約875公斤,1939年盜掘出土于河南安陽武官村,挖掘者是當地農民吳培文。當時河南已處于日寇占領之下,村民想將鼎賣掉,并且不希望鼎落入日本人之手。吳培文等人原本計劃將鼎肢解鋸開,但只成功鋸下兩個鼎耳。日寇搜剿這個出土大鼎,于是吳將鼎再次埋入地下,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后才重新掘出。
司母戊鼎后被運往南京,作為給蔣介石六十大壽的禮物。蔣1948年還攝有一張站在沒有耳朵的司母戊鼎前的照片。解放前夕,蔣介石計劃將司母戊鼎用飛機運往臺灣,由于鼎過大過重沒有成功。1949年,人民解放軍在南京機場發現了被棄置在那里的司母戊方鼎。
司母戊鼎解放后由南京博物院保存。當時司母戊鼎的一只鼎腿上有武官村村民鋸鼎未果而留下的鋸痕,被鋸下的鼎耳經過多年戰亂,也只找回一只。南京博物院委派潘承琳將司母戊鼎腿上的鋸痕填滿,又根據殘存的鼎耳仿造了一個假耳朵,將丟失的耳朵修復“還原”。1959年,配好了假耳朵的司母戊鼎被調撥到中國歷史博物館。
撇開假耳朵的遺憾不談,司母戊鼎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最重的中國古代青銅器,是鼎中之王,是傳國重器。
司母戊鼎四個柱足是中空的。整個鼎的鼎耳事先鑄好后嵌入鼎范(“鼎范”就是用來鑄鼎的模子),再一次澆鑄制成鼎身鼎腿。司母戊鼎在商代晚期制造難度是驚人的。大鼎腹內壁鑄有銘文“司母戊”三個字。1976年安陽殷墟商代婦好墓后出有“司母辛”銘文銅鼎,可以與“司母戊”銘文相印證。
14-4宮樂圖 晚唐絹本縱48.7厘米、橫69.5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中宮女的發式、服裝和開臉留三白(額頭、鼻子、下頜留白不施胭脂)是典型的晚唐時尚。畫面正中的桌子與今天的桌子高度接近,但是當時的桌子主要還是用來置物的。桌子和凳子相配、人坐在桌子旁寫字是到北宋才流行起來的。
唐代以前沒有今天意義上的桌子。唐以前的人坐在席或者矮床上,寫字是左手執卷成筒狀的紙(或者竹簡、木片等等),右手執筆。因為這種和今日迥異的寫字姿態,唐和唐以前毛筆寫字的筆法也與今日迥異。這就是在后世讓大多數人懸隔不知的“轉筆”,也就是字的每個筆劃在書寫時都需要不斷捻轉筆桿。
傳說王羲之十二歲的時候,他看到了前代的寫字筆法論集。而這個論集居然是他從自己父親的枕頭里偷偷翻出來的。到了他晚年的時候,他又寫了“筆勢篇”給兒子王獻之,并且叮囑他“勿播于外,緘之密之,不可示之諸友”。如此月黑風高殺人放火般的揶著藏著,說的其實都是寫字時毛筆的筆桿旋轉。這種筆法到宋代已經大體失傳,只在某些書壇高手家族之中秘密流傳。
又比如,唐代歐陽詢的字方正險絕,筆劃轉折之處如斧砍刀削般剛硬挺刮。今人臨摹,每每以寫到這種位置為苦。其實,這種方硬的轉折都是必須捻轉筆桿才能寫出的。清代法書之首劉墉,在人前寫字時大拇指和食指彎成圓圈狀握筆(所謂“龍睛之法”),顯示自己寫字純用腕力;但是劉墉家的傭人說,當他關起門來寫字的時候,手指不斷來回搓捻轉動筆桿,“筆如舞滾龍”,有時候轉筆太厲害甚至毛筆會脫手掉到地上。今人不察,小學老師教學生寫毛筆字,只知道講王羲之妄圖從兒子手中抽走毛筆未果,從而表揚孩子握筆好這個故事。實際上,這是個非常白癡也絕對錯誤的故事。
舊時人寫字非常注意所謂“開蒙”,也就是老師如何教小孩寫第一個字。畫家羅工柳晚年以寫狂草聞名。沈鵬見到他說:“沒聽說過你寫字,怎么忽然一下子你的字寫得這么好?”羅開玩笑說:“給你開蒙的是一個秀才,給我開蒙的是一個舉人。咱們兩人寫字你就差在開蒙的第一步上了。”這雖是玩笑,但是也說明開蒙的重要性。開蒙給后學提供的,除了抓筆、運筆、字的間架結構,還有這非常神奇的筆法。回頭我們來看今日孩子寫不好字,與其說是孩子不用功不認真沒天分,還不如說是大多數老師無能,根本沒有能力給孩子提供真正意義的“開蒙”。
文章分頁: 1 2


